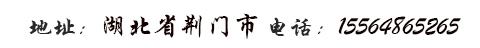父亲的时间表刘江
|
那天走出医院的病房,迎面是壬寅年雨水时节的一场大雪。这春天的雪不像寒冬的雪那样飘逸干爽,洋洋洒洒;而似乎是有满腹的心事和委屈,脚步滞重,跌跌撞撞,稍遇磕绊便是泪水涟涟。脚下明明是皑皑的雪,踩下去却是汪汪的水。就这样,我一脚深一脚浅地走进了小区的绿化带,没想到这林木间竟有一股清冽的暗香袭来,也许是因了这寒雪冷风,这香香得彻心彻骨,使我木木的脑袋顿时清醒了许多。遂香而去,迎面是一树残梅,因了这春雪的滋润,这梅,花虽败,香未尽,有了这雪水的洗礼更加香的纯粹,虽薄犹浓,香气袭人。再细看那残花,头上雪花重重,下垂的花瓣却是雪水滑落如珠。啊!谁曾说“我与梅花两白头”,怎不白头?能不白头?心,立刻化成了一汪雪水。 相庆以米,相期以茶。我们为父亲庆祝八十八岁大寿时,他还是那样的爽言爽语,起居有序,饮食有度,每天两杯小酒,出门不戴帽子,不拄拐杖。他说,一柱拐杖,就真成老头了。谁知刚迈进九十岁的槛,便饮食逐减,精神不振,电子扫描细密的触角抚过父亲的全身,虽然没有确诊有恶性病变,但各种器官的衰退性变化足以让人触目惊心,如临深渊。一家四代内外二十六口人,原计划响应疫情期间的号召,分别就地过年。可得到父亲身体不适的消息,无一例外,飞鸟归巢般扑向他的身边。父亲拖着疲惫的脚步,抚摸着重孙子们的头顶,依然在他们的吵闹中浇花喂鱼。拍全家福的时候,老人家张开双臂,将小可爱们揽入怀中,双目茫然望向天空。湛蓝的天空有飞机划过,白色的烟雾飘带般飞扬。 二弟退休后受聘的医院,因疫情中的一场事故停诊,但对直系亲属开放。借此便利条件,我们弟兄三个一商量便立即带父亲入住。一流的设施,一流的服务,偌大的一个病区连父亲总共只住进了三位病人。 在这神圣的静谧中,医生职业的目光透过镜片望着我,用尽可能平静的声音告诉我:“基本可以确诊,肝门胆管有占位,肝硬化失代偿期,胃底静脉曲张,别说你父亲是高龄,即使是年轻人,我们也不建议手术。你们家属应该有心理准备,这个病发展是非常快的……”那一刻我觉着自己在飞速坠落,两耳能听到下降的声音。 回到病房,望着输液管中药珠缓缓滴落,心中似有木鱼声声敲击,为父亲的生命加持。看着倦卧在病床上的父亲,我想到一个词——剥茧抽丝。我觉着我和父亲都是一只茧,不过是属于父亲的那只茧是被病魔泡在无情的温水里,而属于我的那只茧却是吊在尘世的风雨中。虽然我这个儿子年近七旬,但在心里并不真正清楚,自己的茧衣剥开后,双翅是否已经硬朗得足以搏击生命中没有父亲遮挡的风风雨雨。 天晴了,有道是“东风吹散梅梢雪,一夜挽回天下春。”但从病房的窗户上望出去,终南山上依然是巉岩嵯峨,白雪皑皑。病房里新入住了一位病人,年龄与我同岁,陪同的儿子也恰好和我的孩子同岁。一下子觉得我们这个病房里有了别样的景致,那是生命的阶梯吗?落日的余晖反射在玻璃幕墙上,使这个傍晚多了几分凝重和辉煌。 经过十多天的对症用药和能量补充,父亲的精神好了许多,医生建议出院,父亲也不愿再打点滴了,看着父亲日益消瘦的双臂淤青斑斑,我们也只好随他的心。两位弟弟劝说,天气暖过来了,正是春暖花开,在他们家里都住住,游玩游玩再回去。父亲却说,这一难要是过去了,以后有的是时间……那没有说出的后半句话,我们父子都心知肚明,一时间人人无语。 我明白这是最后一次陪父亲远行,车上备足饮食水果,心想每一个服务区都停停,走走转转,尽量让父亲再多看看这生动的春色。可父亲一路都不愿下车,说赶快走吧,回去就踏实了,在家里吃一碗热汤面比什么都舒服。 父亲在延安住所的院子里绿化非常好,迎春花金灿灿,樱花、玉兰花含苞待放。父亲一生爱花,回到家每天都喜欢坐到花园边晒晒太阳,太阳影子过来时,我说凉了,咱们回屋里吧。父亲总说,把凳凳移一移,出来了,就多坐坐。父子两白头,我们就这样默默坐在玉兰树旁,享受着春天的阳光。 这样的光景享受了没几天,父亲的身体状况又出现了反复,干呕、脸色发黄、日渐乏力,我们医院。这一次父亲的话明显少了,每天总是望着输液的药瓶发怔。总说:“我看这药也和西安用的一样,怎么就不见效了?” 为了使父亲能好好的休息,每天打完点滴我们都给医生请假,接他回家。只用车接了一天,父亲就不愿再坐车了,让小弟用轮椅推他回家。他说,坐在轮椅上畅快,还能看看绿化带里的花。一边看,嘴里还一边不住地念叨:“连翘花开了、小樱桃花开了、桃花也开了……” 一天晚上漱洗毕准备睡觉,父亲示意我闭上门,对我说:“我看了,这病要好是没希望了。瓜熟自落,人活百岁也免不了这一场,我九十了,也没有什么遗憾。我这一辈子,没给你们挣下,也没给你们动下,咱不欠人的,人也不欠咱的。你们兄弟姊妹几个都能顺顺利利的,我也没有什么拽牵的。后事要从容些,不要把帮忙下苦的赶得太紧。保姆走时多给上一点钱,那也是一个恓惶人,下苦人都不容易。你们要吊针,再吊上几天,尽一尽你们的心意。再多了也没用,治不了的病,花钱受罪……”这是我第二次见父亲流泪,第一次是祖母去世的时候。 二弟闻讯立即请假赶回,医生建议做个胆管引流手术,这样可以减轻黄疸,改善食欲。和父亲一说,他坚决反对。他说,治不了的病让我挨那一刀干什么!你们就让我攒攒欢欢地走吧。无奈,只能用药维持。为了节省父亲的体力,二弟又联系了家庭病床,护士每天上门输液。凡有亲朋探望,只要不吊针,他都要穿戴整齐,坐在客厅里和客人拉话,回忆早年旧事。 父亲几乎是茶饭不进了,全靠人造蛋白维持。一天突然很有兴致地对保姆说:“把那盆君子兰端过来让我看看。”他用手轻轻抚摸着厚实的花叶说:“好好当事些,你看这花心鼓鼓的,兴许今年能开。”表情,像是在抚摸一个可爱的孩子。随后问我们:“今天古历多少了?”听说是二月十九,他便扭过头说:“赶紧把老家的地方收拾收拾,我看这拉磨不下几天了,再吊两天针咱们回家。” 我们只当父亲这是随口一说,谁知真只再吊了两天,他是坚决不让扎针了。他对站在床前的护士说:“娃娃,你来了,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你回吧。”见我们不松口他便说了狠话:“怎么,嫌我死得慢吗!”我们,只好含泪作罢。 农历二月二十二那天,父亲说咱们明天回家。在讨论用不用救护车的时候,父亲的态度丝毫不含糊,他对我女儿说:“我知道你们想的是什么。不要救护车,我就坐你爸的车,高高的。”回到家,问他,睡床还是谁炕。他反问:“回到家为的是什么,不就是能热热地睡到炕上么?” 乡亲们闻讯一一前来探望、安慰,他们记着父亲在物资奇缺的年月里给出嫁的女儿买过红条绒、给娶媳妇的儿子买过绸被面、给缺奶的小孙子买过白糖和炼乳……父亲挣扎着和他们一一招呼,轻声叫着他们的名字。 两天后,屋里终于安静下来,一星期几乎粒米未进的父亲突然说要吃酸汤面。妹妹和小弟去准备的时候,他像小孩子一样急不可耐,伸出两只手做捧碗状,不住地问:“好了没有?酸汤面好了没有?”饭,端上来的时候,父亲像长途跋涉的人看到了甘泉,一边贪婪地吃着,一边说:“酸汤面,就是这酸汤面……”那几口面父亲吃得酣畅淋漓,吃得我们兄妹四人泪流满面。往日喝一口水都发呕的父亲,这一碗酸汤面却吃得非常享受,不但一点反应没有,过了一个多小时又问:“那面还有吗,让我再吃两口……” 第二天父亲便失语了,我们兄妹四人只能是轮流分跪在他的两边,根据他的表情不时地给他翻身,但每一个姿势只能保持三五分钟。最后只能将父亲抱在怀里,只有这一个姿势父亲才能多安静几分钟,他那侧弯的脊椎骨像刀背一样硌在你的胸前,似乎有一种切肤之痛,让你真正感受到什么叫骨瘦如柴。这时候,我们儿女的心里犹如有一把双刃刀在来回搅动,一方面觉着,这样延长生命就等于延长痛苦;一方面又觉着这样把父亲带回家眼睁睁地看着无情的病魔在一天天吞噬他的机体而束手无策是一种罪孽,是最大的不孝……当学医的二弟失望地叫着我的时候,懵懂的我依然不相信父亲的病痛会这样戛然而止,更不相信那个给我们生命的亲人,转眼间就会与我们阴阳两隔。我用手捧着父亲的脸,感觉到父亲颌下的脉搏依然还在一下一下有力地跳动。二弟说,那是你的心跳。 送葬路上,山花烂漫,风起处落英翻卷如雨。天云仁兄的挽幛写道:奠基广电,服务乡梓;高风亮节,以昭后人。父亲是宜川有线广播的创始人,他的老同事纷纷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吊唁,追思他们脚蹬自行车肩抗铁丝卷走遍宜川山水,共同创建“户户通广播”的火红岁月,有的不能前来还录了音频,让怀念之声越过山阻水隔传到父亲的灵前。落东村的乡亲们在村口设祭,用切切的乡音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父亲就这样在这如雪如雨、如泣如歌的春光中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安卧在故乡的热土之中。 逝者安息,亲朋返程。安葬了父亲的第二天,疫情四起,新冠病毒的恐惧弥漫宜川全域,随之封城、封村,限制人员流动。真不敢想象,若是迟上一天,该如何给父亲送行。这时间表,是父亲自己安排好的吗?他老人家一生刚正不阿说一不二,宁下苦不受气,做事宁可牺牲自己的前途命运,也从不连累旁人。没想到,就连告别人生也是这样心知肚明,果敢决绝。 图源网络 编辑/小宋审核/王凯 延安市作协投稿邮箱 yananzuojia .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ingchunhuaa.com/ychfz/10104.html
- 上一篇文章: 疫情期间勤充电,共迎春花烂漫时应县农商银
- 下一篇文章: 丰台这个公园建好7年,至今仍未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