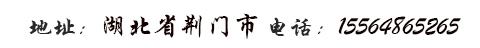你再也伤害不了我了
|
这是STORYBOOK上的系列故事 插画/安娜 生活在这条小胡同中的人,每天都经历着亲情、爱情和友情的考验,面对复杂情感带来的种种困扰,每个人都有最不为人知的一面,或是自私,或是嫉妒,或是憎恨。 随着时日的推移,在成长的道路上,胡同内的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从未有过的羁绊和缠绕,对自我、对爱、对世界的认识有着微妙的变化。 他们不仅是活在故事里的人物,更是现实世界里我们的缩影。 《胡同纪事》第9篇无妄壹 天是昏的,昏黄而沉郁,刚下过的一阵雨也没能让它变得清明。春雨算了算日子,刚过了惊蛰,按理说天应当愈来愈好,然而早起去地里的时候依然寒风萧瑟。 或许以往的许多年都是这样——春天眼看着要来,却始终迟迟未来,等到所有人灰心丧气的时候才突然降临,没完全迎合过大家的希望,却也没叫谁的期望落空过。 今年不知怎的,春雨对一向最钟情的春天忽然没了热情,田边儿的迎春花已经顶着寒风开了蕊,再过一个礼拜,村后面的小土坡就会被嫩黄完全覆盖。 这种花单看起来平淡,一簇一簇地堆在那里倒显得壮观,春雨从前喜欢站得高高的,将所有的嫩黄色尽收眼底。 可去年的除夕,她刚刚将老父亲葬在自家兄弟的田里,几个坟头紧挨着小土坡,里头安放着祖父辈的尸骨,再爬上去看花,就要把列祖列宗踩在脚下,这是对他们的大不敬。 除夕夜死人是个不吉利的事,春雨的兄弟将尸骨在家里停了三天,过完初一才风风光光地下葬,做女儿的在棺材前面哭得死去活来,去外地打工的年轻人都回了家,凑在棺材后的空地上,嗑着瓜子看热闹。 吴根生是在吃饭的时候忽然没的,前后不过一分钟,按本地说法叫做“喜丧”,当儿子的因此省下一把鼻涕眼泪,将多余的精力全放在操持葬礼上,做女儿的要辛苦一点,讲究点的要从咽气哭到下葬,春雨没这个气力,哭了一整夜后眼泪便枯了,头也昏昏沉沉,随时将要晕倒。 这和宋晨生脱不了干系——来奔丧前,他刚刚把厨房里的擀面杖敲到了她脑袋上,只消一下便把春雨给打懵了,痛感后知后觉地蔓延,她缩着肩膀,不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一棍有任何的抱怨。 宋晨生的娘——也就是春雨的婆婆在一边儿吓了一大跳,一巴掌打在宋晨生拿着擀面杖的手臂上,“啪”的一声脆响,其威慑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你做什么?!棍子抡到脑袋上,打傻了怎么办?”她扯着没剩几颗牙的瘪嘴嚷嚷,手里还握着炒菜铲,插着腰站在两人中间,给了春雨一丝喘气的余地。 宋晨生将擀面杖随手扔到砧板上,皱着眉头在狭小的厨房里转了两圈,像是要寻着一个将这顿单方面的殴打持续下去的理由。 然而大多数时间是没有理由的,若不是婆婆拦着,要么是嘴角,要么是鼻子,总要有一处出了血他才肯罢休。 倘若哪天他去哪里再喝上二两酒,那么一整夜她都要死死地将嗓子里的哭声摁回去,绝不能叫紧挨着的两家邻居听到——毕竟家丑不可外扬。 春雨的心随着他的脚步声提了上来,忍不住咽了咽唾沫,她手上还拿着择到一半的香菜,此刻被她下意识地攥进手里,身体也条件反射地绷紧,等待着他如一头疯狗一样冲上来。 两圈,三圈,婆婆嘟囔道:“你不等着吃饭,在厨房晃悠什么?” 宋晨生回过头,眯着眼盯了春雨一下,将她盯出一个小小的战栗,他对这种反应显得十分满意,停顿良久才大发慈悲般地说道:“瞧你吓得那样子,我又不会吃了你——咱爹去了,小弟叫你赶紧过去。” 她浑身一个激灵:“什么?!” 宋晨生瞥她一眼,似乎是懒得重复,披着一件皮夹克,往嘴角塞了一支烟,慢悠悠地出了厨房,往堂屋踱过去。 春雨愣愣地看他的背影,脑子里一片混沌,仿佛还没从方才的那一闷棍中缓过气来,婆婆推她一把:“还杵着干嘛?!快把菜择好,别吃午饭了直接去!” 她看了看手里被攥得不成样子的香菜,匆匆将身上的围裙解下,衣服都没顾上换便跑了出去。 贰 二十九的好日子,天大冷,春雨跑出门好一段时间才觉出身上凉飕飕的,低头一看,身上只穿了件单薄的小棉袄,领边儿裹着一圈无济于事的绒毛,还是暗红色的。 白事上穿红不吉利,可她不敢再折身去换——宋晨生从来不是打完一巴掌就收手的人,她怕回去便要被逮个正着,不由分说地打上一顿。 明儿就是三十,虽然自从嫁给宋晨生之后日子从没被灶王爷保佑,但她还是在心里默默祷告,希望灶台上那位无形的神仙能保佑自己过好这个年。 祷告到一半她就笑自己被打傻了:三十没到就死了爹,哪里还能过好这个年? 过完年,她就三十岁了,年龄的增长于哪里的女人而言都是一种隐秘的凄楚,在春雨这里显得更甚——三十岁了,她的肚子还没有半点的动静。 邻居家的麻子的老婆手里牵着一个,肚子里还揣着一个,麻子吹牛的时候曾讲过:医院做过检查,百分百是个小子。 当时春雨躲在屋后的窗沿下晒被子,听到这话,顺手也把自己心里头翻来覆去的难受晒了晒:迟迟怀不了孕,她也想医院好好检查,看看是不是她的肚子出了什么问题。 和麻子扎在一堆的宋晨生叼着大前门的烟,忽然斜着眼看了看她,嘴角似有似无地一抹冷笑,让春雨心惊胆战。 怀不了孕向来是宋晨生对她施以毒手的最佳理由——从前他打老婆,村前村后难免有看不下去的人来劝架,隔壁几家的婆娘也像模像样地指着他的鼻子骂过,春雨因此得了好几个月的平静日子。 然而好景不长,过了五年,她肚子没半点动静,宋晨生还没说什么,她婆婆先急了,给她连熬了一个月的中药,一日三顿地喝,苦得人眼泪都要流出来,还是没有半点效用。 宋晨生嫌弃她喝完中药后身上的味道,原本就不怎么热衷的床第之事显得更加潦草,春雨躺在他身下,每每觉得自己像头待宰的猪——她见过村里养猪场里的人杀猪,四只蹄子被紧紧捆着,只能发出无意义的哀嚎。 开始时宋晨生仿佛还没发现春雨不争气的肚子是个好理由,仍然隔三岔五地打她一回,他年轻的时候出去浪荡过,打起架来像条疯狗,少有人愿意与他正面对峙,如今落在春雨身上,她更是不敢吭一声。 她在拳脚中总结出了一套经验:被打的时候哭声越大,喊得越惨,落在身上的拳头就越狠,宋晨生打到兴头上的神态很是吓人,一双眼瞪得极大,红血丝蔓延在其中,像小人书里描绘的恶鬼。 村里的汉子聚在一起闲谈的时候,春雨的远房表叔率先表示了不满,虽说嫁出去的姑娘是泼出去的水,但春雨的兄弟对他这个亲姐姐不管不问,春雨又是隔壁村的姑娘,在这村里只有他自己一个帮衬。 话还没说尽,春雨的婆婆便冷笑一声:“打她?晨生打她算是轻的,不争气的东西,五年了没憋出个屁来,买只鸡还能天天蹦出个蛋来呢!” 远房表叔的话僵在嘴角,半晌呐呐地说上一句:“那也不能下那么重的手……” 宋晨生只是闷头抽着烟,看起来沉默又隐忍,简直像个虽然得不了孩子但还坚持没和春雨离婚的好男人。 等到春雨知道这件事后,她不能生的传闻已经在附近几个村子里传了个遍,有半大的野孩子心眼蔫坏,躲在她去地里的必经之路上,从草堆后面窜出来狠狠地拍一下她的肚子,没等她反应过来就一溜烟地跑远,留下一阵肆无忌惮的笑声。 她又气又羞,在田里憋着一口气将农活弄完,等到天落黑后趴在麦田里狠狠地哭了一场。回去后便被宋晨生一把扯住了头发,几巴掌扇在脸上,将她没流尽的眼泪扇了出来。 她的噩梦从这一天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开始,公婆就在堂屋里看着电视,声音开得很大,电视里头是无穷无尽的广告,春雨努力把她的注意力放在那些广告上面,好逃离些身上的痛楚。 婆婆偶尔扭头瞥她一眼,春雨缩在角落里,近乎哀求地看着她,眼角被打出了一块淤青,鼻子也淌了许多血,看上去狼狈又可怜。 “行了晨生,再打下去人就不行了。”往往到了这种时候,婆婆才会轻描淡写地说上一句,落在宋晨生耳朵里像在挠痒痒,往往要再打上十几分钟才肯彻底松手。 春雨不敢哭,也不能哭,抽空回了趟娘家,脸上顶着大大小小的伤也没人去问,大家都对这伤心知肚明,她强拉起笑,将一圈看热闹的人送走,关了门就哭倒在了她爹的脚下。 她被打怕了,鼓起勇气来回娘家,想要和宋晨生离婚。 她兄弟在旁边儿漠不关心地站着,听她说出那两个字便嗤笑:“你是被打傻了还是怎么?跟他离了婚,还会有谁要你?” 春雨哭着摇头:“不,我回来伺候咱爹,这辈子都不嫁人!” “你说得倒是轻巧,”弟媳妇斜着眼推门进来:“我们一家子吃饭都还顾不过来,难不成还要再养你一辈子?!” 叁 回娘家不过两天,春雨便回了家,同她一道回去的还有她爹,颤巍巍地拄着拐棍,冷着脸从邻村走到春雨的婆家。 春雨在他身后小心地跟着,脸上的几道伤已经结了痂,摸上去磕磕巴巴,有些不舒服,她在心里安慰自己:还好这是最后一次了。 他们本来是不存在什么离不离婚的——春雨嫁给宋晨生那年还不到十八岁,去镇上的民政所也领不出来结婚证,好在婚礼办得体面,下轿礼是六百六十六,当时的年岁,在临近的几个村里都算是很大的手笔。 春雨接了礼钱,眼睛蒙在了红色盖头下,右手被转到了一只陌生又温暖的大手里,她心跳得厉害,将红包攥的死紧,腿也发软。 这门亲事,是她父亲为她定下的,理由再简单不过:宋晨生回来的头一年就添了辆拖拉机,“吭哧吭哧”地在田间作响,那是财富的象征。 况且他脸也长得周正,除了个子不争气——勉强有一米七零,又瘦又小,像个半大小子,其余的与春雨都算得上是门当户对。 媒婆来家里说了两次亲,第三次春雨便被宋晨生约出门见面,两人在村里胡乱逛了一天,当天夜里春雨便通红着脸应了这门亲事。 结婚的头几个月,宋晨生表现得很正常,春雨的婆婆长着一张和善的老人脸,牙还健在,是个消停不下来的老婆子,家里的闲活被她揽下大半,春雨整日里吃吃睡睡,腰身松了一圈。 回娘家探亲的那几天,逢人便会夸她好福气,嫁了吃喝不愁的一户人家,这辈子都衣食无忧。 可半年没过,宋晨生便彻底像变了个人,先是动不动训斥她几句,隔三岔五地动手,春雨开始时还有底气,每逢挨了打便哭着往娘家跑,住满一个星期,等着宋晨生低三下四地跟过来,求她跟自己回家。 后来这一招不再顶用——她兄弟成了亲,弟媳妇是个眉眼尖利的女人,看不惯春雨哭哭啼啼的样子,将大门落了锁,任她拍打一下午都不予理会,打小玩到大的姐妹偷偷劝她:“总是这样也不是办法,都是嫁出去的人了,老回娘家会被人说闲话。” 她顶着一脸的伤,灰溜溜地回了婆家,当晚便又遭了一顿打。 婆婆大约也看不惯她隔三岔五回娘家,头一次没站在旁边劝架,等春雨哭到声嘶力竭才冷冷地拿眼瞥她,将洗脸毛巾甩到她身上,叫她好好睡觉,别再想那些有的没的。 春雨用毛巾盖着红得发热的双颊,不懂她说的那些“有的没的”是什么意思,骨子里却被打出了恐惧,仓皇地从地上爬起来,将自己勉强收拾利落。 她的日子仿若从天上跌到了地下,围绕着她的只有一日三餐和不期而至的一顿打,她在心里盼望着宋晨生和村里的大多数年轻男人一样,能出门随便寻个活计,十天半个月,不,整年整年不回家都不算什么。 只要她不再挨打,就算宋晨生像那些常年在外做工的男人一样,家里守着一个,外头养着一个也没什么要紧,她不再抱着那些少女的期待,甚至隐隐有些羡慕村里独守空门的婆娘们。 门从里面被打开,宋晨生的脸在晨曦的薄雾中犹如鬼魅,他生得白,又常年窝在家里,不见一点儿阳光,因而显得更加苍白,春雨躲在她爹身后,连抬头看他一眼都觉得惊悚。 “哟,您老怎么来啦?”宋晨生将一支大前门叼在嘴里,倚着门框眯起眼笑,并没有迎他们两人进门的意思。 春雨壮着胆子,手却抖得厉害:“咱爸来了,你杵在在门口干什么?” 宋晨生站在门槛上,比春雨高出了一个头,眼皮子耷拉下来,居高临下地看了她一会儿,将门让出一条缝来,春雨跟在她爹身后,缩着肩膀听见了关门的声音。 “咔嚓”一声,惊出她浑身的冷汗,堂屋里的灯昏暗的一盏,将门洞照得更黑,她脚底生出一股凉意,踏过门槛时像跨进了一只巨兽的嘴里。 肆 春雨到底没能离了婚。 吴根生在宋家坐了小半个钟头,从兜里摸出了一盒藏了许久的茶叶——那还是几年前的春节一个远房亲戚送的,一直被他留到现在,如今放在了宋晨生的面前。 宋晨生将茶叶盒来回看了看:“我不喝茶。” “没事捏杯子里几撮,权当提神。”春雨瞧见她爹脸上挂出的笑,心里万念俱灰。 宋晨生懒洋洋地将茶叶盒放下:“爹你吃了没?让春雨给你摊两个荷包蛋?” “不了不了,这就回去。”吴根生脸上的笑从进门开始就没揭下来过,拄着拐棍就立刻要走。 走到门口时冲呆愣在偏门口的春雨使了个眼色:“你来,我叮嘱你几句。” 春雨往前走了两步,看见吴根生脸上的神色,泪便止不住地下来。 吴根生尴尬地拍了拍她的胳膊:“多大个人,吵个架还要跑回爹跟前哭?”他语气里带着笑,浑浊的一双眼里落了满满的无奈:“听爹的话,以后跟晨生好好过——晨生,我走了啊。” 春雨记得,他这一走就是许多天。再见他时,两人之间隔了块厚重的木板,她昏着脑袋,拍打着板子几乎要将肺腑都随着眼泪哭出来。 棺材板前的长明灯摇摇欲坠,春雨在几乎将人冻僵的寒冬里穿着薄袄守了三天两夜,下葬那天终于没能撑住,直愣愣地倒在了仪仗队前面。 后来醒了,头上破了一大块,村里的人都说:这是个孝顺女儿。 只是可惜命里苦,生不了孩子。 春雨从凉意中猛然惊醒,下意识地打了个寒战,初春的天寒气浓重,但阳光太具有欺骗性,以至于她躺在土丘上睡了许久才被湿气冻醒。 她将身上的杂草拍下去,揪了几把刚盛开的迎春花,捏在手里随意地把玩,脚底下正对着的便是吴根生的坟,紧挨着他的是她早逝的母亲。 春雨心想:总有一天,自己也会被葬在他们的身旁——不,不会的,她嫁给了宋晨生,就连死也要埋进宋家的老坟。 这些年来,她每每想到这里心里便像堵了一把棉花,她生过不上好日子,死了之后也许还要继续被宋晨生毒打。 她蹲在土丘上,漫无边际地瞎想:不晓得人的魂究竟还有没有痛觉,如果像鬼故事里形容的那样轻飘飘的,兴许宋晨生一脚便能把她打散,散在天地间,是再好不过的事。 她站起身,将搁在衣服夹层里的一张薄薄的纸拿了出来,眯缝着眼背着阳光看了又看。 那是一张检查报告单,她挑了个宋晨生好不容易离家的日子,医院做了检查,又央医生替她看了看。 上头写的什么,她不大懂得,只知道那医生张口吐出一句轻飘飘的没问题,便将报告单甩了回来。 回村的路上,春雨将小小的一片纸藏了又藏,终究还是觉得不保险,索性来到吴根生面前,将报告单烧给他看。 风吹得急躁,火苗舔上报告单,几秒钟的功夫便烧成了一小撮灰色的粉末,随风扬了起来,顷刻间消失不见。 她循着那些粉末仰头看了会儿天,裹了裹身上的衣服便往家去:留给她的时间不算多,公婆去了邻村喝喜酒,宋晨生被以前的伙计叫了出去,多么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她的心砰砰跳着,刹那间觉得自己仿佛重新活了过来——这些年来在宋晨生的拳脚之下,她已经麻木得如同拳击手面前的沙袋,无休止地挨着一拳又一拳。 村里的几个闲汉迎面撞上她,嘻嘻哈哈地打量她几眼:“春雨,你家男人呢?” 她心里恶心这几个流里流气的男人,却不自觉地挂上笑:“谁知道跑哪野去了?” “哟,你说这话小心他回来又揍你!” 春雨满不在乎地笑了笑,加快步子将他们甩在身后。 伍 结婚十余年,她对这个家了如指掌,尽管宋晨生残暴得像个施虐狂,却很少管春雨的花销:宋家本不缺钱,宋晨生总有弄到钱的门路,偶尔心情好的时候会甩给她几张鲜红的纸钞,半是施舍半是补偿。 春雨暗自揣摩过他的这种心思,最终只能得出唯一的一个结论:他打老婆的坏名声已经传了出去,若是春雨跑了,或者死了,十里八乡怕难再有愿意嫁给他的女人。 她拉开双人床一头的抽屉,从抽屉深处摸出一个小盒子,紫铜色的外皮已经被刮花了,轻轻一晃里头就叮当作响,那是春雨的全部家当。 一对耳环,银的,自从被宋晨生揪豁了耳垂后就没再带过,结婚时的“三银”一直好好地放着,隔一段时间就被她拿出来,细细地将上面的一层银锈磨掉再放回去。 压在盒子最底下的,是一叠新旧不一的纸钞,五十一百的凑在一起,纸钞下面还衬着一块红色的布,那是她做新娘子时的盖头,质量不错,到如今居然还鲜艳着,刺痛她的眼膜。 她将首饰包在盖头里,钱卷成一团,又镇定地进了偏屋——前些日子打扫卫生时她刚刚翻找过,老两口的体己钱全放在枕头下面,加在一起有小一千,被她一股脑塞进了自己兜里。 另一只兜里装着一张预先买好的车票,目的地是个春雨从未听过的地方,不仅她没听过,在她印象里村里也从没有人去那里打过工,二十个小时的大巴车途径三个省,即将载上她这只被折断了翅膀的鸟。 她压制住自己的雀跃,将屋里的棉被叠整齐,又把院子里的两头猪慢悠悠的喂了,衣服也洗出来全晾在了绳上。 一切看起来都那样平常,仿佛这不过是她生命中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午后,只是锅里的米还是生的,火也没点起来,而她将头发拢了又拢,踏着黄昏的最后一丝余韵往村口走去。 村口到路边搭车的地方显得那样的短,春雨拦下车便有些后悔,坐在三轮后座上忍不住回头望了望身后,想着刚刚应该去跟爹娘好好告个别。 罢了,她将屁股放回板凳,心道:以后的路还长,以后逢年过节冲着家的方向烧几刀纸钱也算是祭拜——她做女儿做了三十年,终于是时候做个人了。 三轮车走得很慢,也并不稳当,春雨的心随着细小的石子来回颠簸,一闭上眼脑子里就全是宋晨生沉着一张苍白得宛如死人的脸站在她面前,扬手就要给她一巴掌。 “去哪?!”三轮车主迎着风吼道。 “汽车站。” “什么?!” 她稍稍提高了声音,仿佛怕被别人听见:“汽车站。” 那人回身瞄她一眼:“天都快黑了去车站做什么?” 春雨愣了愣,嘴边不知怎得就秃噜出一句瞎话来:“今天周五,我去接我闺女。” 那人了然地点点脑袋,一拧车把飚了出去,冷风哗啦一下扑在她身上,将她抱了个满怀,春雨被冻得嘴唇青紫一片,看着愈来愈暗的天色,简直想要振臂高喊。 不,还不到时候。 她摸摸兜里的车票,将它小心地抽出来,攥在手里,像是攥住了后半生所有的依靠。 陆 车站里人多如蚁窝,涌动着簇拥出一些暖意,春雨坐在一大群年轻人的身后,尽量将身体缩在大堆行李的后面,将头埋在两腿之间,像是只遇到天敌的鸵鸟。 熬到八点,终于到了她坐的那班车,春雨昏昏沉沉地跟在众人身后,只觉得身子轻飘飘的,脑袋却很重,但她的意识还很清醒,知道自己就像秋天里最后一批灰蛾,将要扑向烈火。 总之横竖都是死——死在火里也总好过死在宋晨生的脚下,或者吴根生的坟前。 唯一让她觉得庆幸的是,宋晨生到现在也没追上来,扯着她的头发将她拽回去,她坐上车,局促不安地等待着车的启动,眼睛在不远处的人群中来回扫射,心惊胆战地搜罗着任何一个与宋晨生相似的身影。 车就在紧张不安中镇定自若地开了,半躺的座位上面配了一床被子,春雨将弥漫着一股臭脚味的被子拽了下来,整个人埋了进去,深呼吸了好几口,直到快要窒息才掀开被子大口喘着粗气。 检票员就在她身边站着,看神经病一样看她一眼,操着口音浓重的普通话,叮嘱所有人系好安全带。 春雨坐直了身子,照着她的话做,随后扭过头直愣愣地望着窗外不断后退的夜色,一直望到了旭日初升,又再次夜幕四合,熟悉的乡音被另一种陌生的方言所代替,她成了彻头彻尾的异乡客。 这座仓促之下挑选的城市比她想象中的还要更大更繁华,路灯不要钱地亮着,将路两旁的绿化带衬得极漂亮,春雨惊讶地发现里头种了几株迎春花,白天大概已经热烈地盛开过,此时半闭合着,叫春雨心里生出股亲切感。 她站在栅栏旁看了好久,直到有人拍了拍肩膀,拍出了她一声惊恐的叫喊。 “你喊什么?”站在她对面的中年妇人皱着一双描得过重的眉毛,配上白入墙漆的粉底,一双猩红的嘴唇在路灯下煞是惹眼。 “外地来的?”她问。 春雨防备的盯着她,并不准备开口说话。 “来打工吧?一看你就是北边来的。”中年妇人自顾自地说着,手里拿着块白板,上头歪歪扭扭写了几行字。 春雨定睛看去,是几条潦草简单的租房信息。 春雨咽了口唾沫,操着别扭的普通话问道:“房子,房子怎么租?” 中年妇人七扭八歪地领她到了一个小胡同里,胡同一看就有好多年头,地砖上生了潮湿的苔藓,踩在脚下有些滑。 “喏,就剩最后一间,一楼一室一厅,押一付三,一共两千。”女人眯着眼拿出一串钥匙,将红铜色的门打开,进去摁开了灯:“你自己住绰绰有余——对了,是你自己住吗?” 春雨跟在她身后走了进去,屋里东西简陋,只有一个铁艺的水盆架,一张单人床,一个破破烂烂的衣柜,剩下的便是三面墙漆斑驳的承重墙。 “是我自己。”她蹩脚地学着女人的普通话,磕磕巴巴地说道。 中年女人有些诧异,嗤笑道:“自己一个人出来做工,也不事先打听好,就今天这情况,”她撇撇嘴,洋洋得意道:“幸亏是遇了我,搁别人手里,非狠宰你一顿!” 春雨已经顾不得她在说些什么,满心满眼都被这小小的一间房子所占据,手里的钱刚好够三个月的房租,她索性一股脑地交给中年女人,拿了钥匙干净利落地关上了门。 门后贴着一块破了一角的镜子,春雨冷不丁地从里头望见了自己的脸,头发乱蓬着,嘴唇也干裂,一舔就是一阵细小的疼痛。 她怔怔地看着,像是在端详一个陌生人。 柒 夜晚六七点,正值晚饭,小胡同里弥漫着饭菜的香气,有小孩的嬉笑声从开得过矮的窗前飘过,恍恍惚惚的像是梦境。 哭声先是细微地响起,隐约地飘散在空中,像是怕惊扰了旁人,随后一阵大过一阵,将小小的出租屋塞个满满当当还不够,直惊得窗外的野猫都沿着围墙窜去了别处。 春雨将大半张脸埋在潮湿的床褥上,眼泪一阵一阵地窜出来,全然不受她的控制,身在几千里外的异乡,她仿佛沿路拾回了许多勇气,不再忧惧哭声太大会丢了脸面。 她枕着一屋子旧日的眼泪,终于沉沉地睡去,等到朝阳再度升起,门窗大开,所有旧日的阴霾便会如她所愿,在初春足够宽容的阳光中彻底消散。 冬天终于结束了,有的人死在了寒冷中,而另一些人将要迎来姗姗来迟的新生。 -09/END- ——— ▍前文回顾第一篇:北京方便面之味 第二篇:当你孤单时你会想起谁 第三篇:无疾而终 第四篇:杀死那只猫 第五篇:阿胖 第六篇:展信佳 第七篇:柔和七星 第八篇:背叛 作者:温难(微博: 温难酱酱)活着是为了燃烧,燃烧是为了让灰烬留有意义。 更新频率:每周一更 声明:本系列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及使用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ingchunhuaa.com/ychpz/5651.html
- 上一篇文章: 战ldquo疫rdquo,迎春花
- 下一篇文章: 法京涛来不及变老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