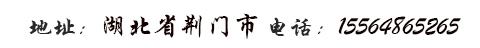宁海莉想起我小脚的婆
|
那天下乡,在托卜务村子里一个商店里,见到了一个小脚老婆,让我一下子想起了我的小脚的婆,也是那样的三寸金莲。婆健在的话,都该是百岁老人了。婆,都去了四十多年了! 从我有记忆起,婆总是干干净净的。她个子不高,那双眼睛不算很大,却清清亮亮水汪汪。一双小脚,扎着裤腿,老式的大襟衣服,头上梳着纂子,网着络子,浑身上下,清清爽爽。不论是冬季的大襟棉袄,还是夏季的月白色大襟单衣,穿在婆的身上,总是熨帖的,没有皱纹,没有落发,虽然她带大了几个孙子孙女,也没有孙辈沾上去的饭渍、口水。她收拾过的房间,如同她本人一样,清爽明亮。婆是个苦命人,爷被抓了壮丁一去不回,从她二十多岁到去世,也不知道爷到底还在不在人世?婆守着唯一的儿子,我的碎爸,和她的侄儿,我的爸爸。所以,我的爸爸和三个姑姑,都把婆叫“娘”。人常说“三岁记老”,我三岁多时,妈妈生了病要去住院治疗,无人照料我。当时婆已跟爸分家,婆就让我每晚和堂姐跟她睡。“咪咪毛,上高窑,把你妹子给我哥,我哥嫌你妹子黑,格磨格磨(geimo)可走呀”或是“小小子,拉风箱(xian),你舅来了吃啥饭?羊肉包子下挂面,把你舅憋死我不管”,在婆低低婉转的童歌里,我在睡梦里吃到了包子,直流口水,而当我香梦犹酣时,却感到婆总是辗转反侧……早上婆给我和姐姐梳头发,一口一个“我娃”地叫着,现在我也喜欢把小孩子叫“我娃”……记得爸爸还在时,每当说起了婆,总是泪光盈湿了眼。说婆做的饭好吃,哪怕是调一碟子红白萝卜丝,也总会调制出不一样的味道来。婆烙的锅盔,有一拃厚,两面黄黄的,花花上得很匀称。婆用盐醋辣子调的素汤,让已灰白了头发,儿孙满堂的付伯伯,称赞回味了几十年。我还记得,堂哥只吃婆调的干面……婆不仅锅灶好,纺线、浆线、经布、织布也是一流好手。娘是在婆的指导下,学会纺线织布的。而我的大姑二姑是在婆的指点下,学会了农村家庭主妇所有该掌握的技能,而且样样都很出色。婆还会花花牌和麻将呢。爸爸在时,常爱和几个好友掀“花花”牌,我时常看不懂,光听他们说“三牛一摆”,“双鱼”,“对戏”,争得不亦乐乎。“每晚汤喝完后,娘把到处收拾好,关了头门、二门,点上油灯,就给我弟兄俩教牌,教打麻将。”爸眯着眼,似乎又回到了娘的身边……为了打发漫漫长夜,婆就和两个儿子用牌和麻将来消磨时间。爸爸学会了打牌,碎爸精于麻将。而麻将也成了碎爸和婶娘争吵的根源。柴米油盐的日子里,拮据艰难的困顿里,又有谁家没有一地鸡毛的无奈呢……我的小脚的婆啊,孤儿寡母的日子里,在家业凋零的困苦里,你是怎样含辛茹苦,用你一双大门不能出,二门不能迈的纤纤小脚,毅然决然撑起了这个家?尤其两个儿子还未成年时,下雨天的井台边,你又是怎样艰难地绞水并提到厨房的呢?你留给了儿孙辈无穷无尽的念想和仰慕啊!而又是什么支撑你苦苦守护着两个儿子,看到他们娶妻生子,你却猝然去了,只有六十多岁!我的小脚的婆啊,至今还有人在夸赞你贤惠能干,又对你无限崇拜啊!可谁知道?自从爷走后,沓无音信,三十多年间,一万多个日日夜夜,纵然有两个未成年的儿子陪在身边,你心中的苦又有谁知道呢?“鱼沈雁杳天涯路,始知人间别离苦”。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两句诗时,我觉得这应该是婆的真实写照。而已去了的婆,躺在村子北面的坟地里四十多年了,她的两个儿子也去陪她了。想来婆再也不孤单了!婆啊,我的小脚的婆!我想你了。说明:网络配图,起示意作用,非作文中老人照片。往期阅读●宁海莉|迎春花·红酸枣 个人 简介 宁海莉,笔名灵犀,喜阅读,爱旅行,用朴实的文字,记录生活里的点点滴滴,捕捉生活中的美。 《雍州文学》编辑部 欢迎您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ingchunhuaa.com/ychpz/7243.html
- 上一篇文章: 找春天第一期
- 下一篇文章: 河北保定邬小径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