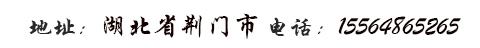故事姐姐死后,我被一道圣旨送进了宫,可我
|
我的孪生姐姐,死于我大婚的前三月。 她死后,我的姐夫,一道圣旨便令我入了宫。 程家的小将军,我原本的未婚夫婿,自这一年起,再也没有回过帝都。 那个英姿勃发的少年郎,只是我的梦中人。 1 我跪伏在地上,鼻端浮动着浓浓的龙涎香。 明黄的下摆拂过我的手背,一只手伸到我眼前,手的主人沉声说:“起身吧。” “谢陛下。”我站起身来,任由他打量着我。 长久的沉默后,他不容置喙地吩咐:“不要穿这个颜色。” 立刻便有宫婢簇拥着我去更衣。 我尚且懵懂,但宫里的风向,还有谁比她们更清楚呢? 我垂首看着身上簇新的衣裳,鹅黄色,轻柔如初春枝头轻颤的迎春花。 这是姐姐钟爱的颜色。 我与姐姐是孪生子,娘亲常说,我们姐妹俩什么都一样,唯有性格和喜好不同。 姐姐温柔娴雅,琴棋书画样样拿手,几乎是帝都里所有大家闺秀的典范。 而我跳脱难驯,琴棋书画只摸了个边,嗯……我是帝都里所有千金们的反面教材。 娘亲念叨我最多的就是:“你这个样子将来怎么嫁得出去!” 不过她并没有为此烦恼多久,姐姐嫁给了太子,少年夫妻十分恩爱,而后不久,太子登基成新帝,而姐姐自然被封为皇后。 我与姐姐的容貌丝毫无差,在姐姐封后那一刻起,我的人生便有了结果。 娘亲不再念叨我,而开始频频叹气。 我不明白,有这等好事,作什么要唉声叹气呢? 姐姐生下第二个孩子时,我已经是帝都有名的老姑娘,当然他们只敢背地里说。 我常常进宫陪伴姐姐,姐姐偶尔会握着我的手,用内疚的眼神看向我,我知道,姐姐心里很不好受。于是我反握住姐姐的手,诚恳道:“我本也不想嫁人,我就喜欢这样自由自在的。” 不久,陛下赏赐于我,金银珠宝倒是其次,当我看到还赐了一座城外的跑马场给我时,我欢喜得一蹦三尺高。 当场便打发府上的小厮去程将军府上,告诉程京那个小纨绔。 果然他拎着我们府上的小厮就上门来,他屁颠屁颠地笑得一脸不值钱的样儿,搓着手问:“沈家妹妹,能不能让我去跑马场玩玩?” 我把头一扬,摆谱道:“那我日前说的…………” 程京狗腿道:“明早奉上明早奉上,我现在就出城,明早城门一开就给你送进来,热乎新鲜的猪血面,一滴汤都不会洒!” 我露出一个得逞的笑,程京揪了一下我的辫子,没等我骂他,一溜烟就跑了。 陛下如此厚赏我,一是为了开解姐姐,二是因为我识相。 而帝都之中,各家小姐因着姐姐的关系,也都对我礼让三分,我也很少参加各府的宴会,不管她们背地里怎么说嘴,至少明面上,我到哪儿都玩得很舒心。 这样的日子,简直比神仙还要快活。 我原以为,我可以一辈子过这样的日子。 2 我进宫后,程京没有再回来过。 我将程京给我的玉佩交给陛下,恳请陛下替我还给程京。 陛下神色莫辨地看了我半晌,点了点头。 我不动声色地松开紧攥的手心,已是一片滑腻的冷汗,我知道,我赌对了。 这样的东西,只有经由陛下的手还回去,日后才不至于惹出麻烦来。 即便如此,陛下依然有几日不再来我的宫殿。 有宫婢劝我出去走走,她们是想让我偶遇陛下,向陛下低头认错。 我心中一片冰凉,我有错吗? 折去双翼的普通鸟雀,要如何变成这奢华巨笼中的金丝雀呢? 我大约是伤心糊涂了,这天夜里,我梦见了程京。 我二十岁那年,程京正为不能随父兄驻守边关而闷闷不乐,他烦得都快把我家的桂花树揪秃了。 我翻着白眼骂他:“帝都多好玩啊!干嘛要去边关吃沙子啊!” 程京狠狠敲了下我的脑袋,严肃道:“这样的繁荣景象是需要很多人去竭力守护的!” 我涨红了脸,第一次不知道如何反驳他。 也不知为何看到和往常不一样的程京时,心跳为什么越跳越快。 我只是懵懂地往嘴里再塞了一个甜玉团子。 梦境里,我泪流满面。 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留下一个模糊的背影,越走越远。 我痛苦地呼喊出那个名字:“程京!” 睁开眼,陛下静静坐在我的床边。 后背倏然冒出一层冷汗,我一言不发地看着陛下,他大半张脸都被阴影笼罩,烛火忽明忽暗照进他漆黑的瞳孔。 我的嗓音绵软沙哑:“陛下。” 陛下按住我欲掀锦被的手,那种触感令我汗毛倒竖。 他问:“哭成这样,可是做梦了?” “是的,陛下。”我直直看向他的双眼,继续道,“梦见妾在家时的事了。” 他不喜欢我自称妾,却也不许我自称若清,他以我来替代姐姐,又不许我默认自己是替身,也不许我真的替代姐姐。 我好像一个失去躯壳的幽魂,既不是沈若清,也不是沈若沅,那我到底是谁呢? 果然,他听见我的自称便皱起眉,一言不发。 良久他才开口:“朕可以准许你再见程京一面。” 我的泪水扑簌而落,我听见自己哽咽道:“不。” 陛下深深看了我一眼,说了句“你以后不要后悔”便离去了。 很长一段时间,陛下没有再来,宫里的风言风语传得厉害,即使我闭门不出,依然能听见只言片语,女人们拈酸吃醋起来,言语堪比利刃。 她们认为我这么个草包仗着姐姐的势,在阁时就张扬不羁,后来又入了宫,陛下因着姐姐待我格外特殊,现在总算被陛下冷落了。 何况我还曾有婚约在身,我入宫这件事,显得她们是个天大的笑话。 终于有按捺不住的,叩响了我的宫门,特意前来将这些话,拐了几个弯当面说给我听,面上还要装出一副懵懂无知。 我对她招招手,笑着说:“太远了听不真切,坐到我身边来。” 她娇笑着起身,眼中闪过轻蔑之色,大概肚子里在骂“草包就是草包”吧。 我看了看她如玉的小脸,叹气:“真是让人好生心疼啊。” 她不解,这次是真不解,不是装的。 我转了转手腕,扬起手,狠狠扇了她一个耳光。 3 晚膳过后,宫婢方瑛告诉我,陛下呵斥了邓贵人,说她挨了耳光正好长个教训,已令邓贵人禁足反省了。 至于我,方瑛没说,自然是还没有处置。 足有半年,陛下再没来见我,我明白,这就是对我的处置。 虽然陛下没有下令禁足,可我也从未踏出宫门半步,留英殿日渐沉寂,只有鸟雀在枝头啾鸣,入冬后,连鸟雀也不再来了。 我伏在榻上,方瑛在榻下放了一个炭盆,我嗤笑一声:“我不怕冷。” 方瑛面不改色,恭顺道:“冬日暖和些,不是什么坏事。” 怕冷的不是我,是姐姐。 我曾窥见过还是太子殿下的陛下,将姐姐牢牢拥在怀里,他低声问姐姐:“若清,手怎么这样冷?” 姐姐娇小的身躯淹没在男子宽阔的胸膛中,她双颊红透,又急又羞说:“殿下!快放开!” 太子殿下的声音充满了蛊惑,他低笑着:“那你叫我一声季盛哥哥可好?” 白雪红梅送清风,女子低不可闻的一声“季盛哥哥”被风吹散,散进了陛下余生每一个思念她的梦里。 命运挥下屠刀,斩断了美好的希冀,留下了永不痊愈的伤痕。 我问方瑛:“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今天原本是我的大喜之日。” 方瑛吓得扑通一声跪下,全身都在发颤。 紫禁城里仿佛住了一只隐形的凶兽,稍有不妨它便会扑出来吃人。 我病倒了。 意识清明的时候,我死死咬住自己的唇,不让自己喊出那个名字,咬得嘴唇都破了,有一只宽厚的手轻轻抚过我的唇,停顿了几秒,又拿开。 养病的日子里,方瑛被带走了,替代她的,是另一个叫方珏的宫婢。 我变得愈发沉默,这场无声的对峙中,我被至高的权力压得难以翻身。 方珏劝我,和陛下服个软吧。 我只是摊开手掌给她看,我问她:“这是什么?” 方珏迟疑了,我不以为意,我告诉方珏,这是我刚刚接住的一片雪花。 现在已经融成手心里的一滴水。 陛下不愿意把我和姐姐区分开不要紧,宫里的女人们明白我到底是谁就行。 程京以前说过,既入樊笼,寸土必争! 我要这座皇宫里有一个位置是为我而留,我要她们不能染指姐姐留下的东西。而首先,我要拿到最关键的那样东西。 长达半年的对峙终于为我赢得了一个机会。 年后,我等来了那道等候已久的圣旨。 再次出现在陛下身边时,我已受封贵妃,赐六宫之权。 姐姐的两个孩子终于交由我抚养,她的长子季惟已经七岁,幼子季恪刚满三岁。 阿恪不太记得我了,阿惟已红了眼眶。 我紧紧揽住他,我无法抚慰他内心的痛苦,这个小小的孩童,刚明白一点人世间的道理,就要遭受丧母之痛。 我才知道,他们俩这段日子是与陛下同吃同住。 我不由怔住,姐姐是因难产而死,肚子里的孩子也没能生下来,所以起初,陛下有一段时间不愿意见到这两个孩子。 次日,陛下来时,我的桌上多了一碟雪沙红豆糕。 他默然许久,眼中有一闪而过的水光,这是姐姐最爱吃的点心。 “我不愿意利用姐姐来得到一些东西,陛下,我们心中有同样的痛。” 像是对他解释我半年来的任性,我哀求地看着他的眼睛。 陛下什么也没说,走之前去看了两个孩子。 他还是不愿面对这残酷的现实,陛下就像一个在台上看戏的人,明明知道是假象,却因身在其中而沉沦。 我紧闭许久的宫门打开,开始接受嫔妃们的拜见。 我还召了娘亲进宫,她摸摸阿惟,又摸摸阿恪,最后摸摸我,泪水怎么也止不住,不敢放声哭,只得捂住嘴,发出幽幽地呜咽。 我替娘亲擦拭泪水,娘亲的泪落得更急了。 我心中酸涩,眼眶涨热难忍,我们三个都在宫里,娘亲必定日夜饱受煎熬。 娘亲走时,紧紧拉住我的手,嘱咐我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好我两个侄儿,我强忍着眼泪点头,目送着母亲在长长的宫墙下越走越远,拐个弯便不见了。 夕阳投下昏黄的光影,斑驳摇曳。 初夏时,阿恪也要入学了。 阿惟教阿恪描红,阿恪胖胖的短胳膊拿起笔来很是滑稽,他涂了一个又一个的墨团,阿惟向陛下告状,陛下便将阿恪抱在膝上,大手握住阿恪的小肉手,一笔一画地教他写字。 阿惟告诉我,歪歪扭扭的两个字是,若清。 我摸了摸阿惟的头,什么也说不出来。 阿惟伤心地问我:“小姨,母后真的不会再回来了吗?” 我抱着他们两个,指着天上亮晶晶的星星,我同他们说:“母后她变成了天上的星星,每天都看着你们呢。” “阿惟、阿恪,喊一声母后吧,母后若是听见了,就会让星星一闪一闪地亮。” 阿恪大声地喊,而阿惟把脸藏在我背后,带着哭腔低低地喊了一声。 夜空中,星光此起彼伏地闪烁起来。 回首时看见陛下站在不远处,晚风吹起他的发丝,拂过脸颊,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无端就让人觉得悲伤。 他醉倒在我殿中,攥着我的手,喊着姐姐的名字,睡梦中,他的眼角滑下一滴泪,在这样的夜里,帝王的伤心和脆弱一览无余。 那个不可一世的小纨绔,风雪交加的夜晚,是否也像这样流过泪呢? 程京。 边关的月亮,也和帝都一样圆吗? 边关的朔风,吹在脸上真的很疼吗? 边关…… 边关没有我,你过得好吗? 我把脸深深地埋进被褥里,良久,发出一声长长的抽泣声。 宫墙外的梆子声远远响起了。 4 七月初一,是我和姐姐的生辰,也是我进宫的第一个生辰。 往常在家时,都是和姐姐一起过生辰,姐姐出嫁后,我便邀程京来一起过,他送我的生辰礼总是稀奇古怪的。 今年是一只四肢可以活动的木雕狗,明年又是一把可以在木柄处塞香粉的扇子,也不知道他怎么寻来的。 程京没有姐妹,他的父兄又都在边关,他不耐烦和他娘待在一处听唠叨,天天都像长在了我家似的。 他从小到大做梦都想能跟着父兄一起去边关,但是我曾听见父母夜话时说:“程将军留下这个最小的儿子,养得上不了战场,用心良苦啊。” 我没藏住话告诉了程京,他难过了好些天。 我安慰他:“不去就不去吧,就在帝都当个纨绔子弟不也挺好的吗?” 他红着脸瓮声瓮气说:“我留在帝都就永远无法娶你啊!” 他在说什么啊这个混账! 我人生中第一次手足无措,眼睛都不知道看哪儿,浑身上下都憋出一层薄汗。 我结巴道:“谁谁谁谁谁……谁说说说要嫁你啊!” 那个小纨绔勾起唇角,俯身笑眯眯地看我通红的脸,说:“你你你你你你你呀~” 他的声音如热烈夏日里的风,既温柔又霸道。 我捂住又红又烫得脸起身飞快地跑,程京在身后哈哈大笑,我的唇角不由自主地上扬。 我的婚事艰难,可那时的我们,尚且还有一搏之力。 晚膳后,方珏伺候我沐浴更衣,我看着镜中人,一时有些恍惚。 何年,何地,何人呢? 方珏随我一同上轿,好似走了很远很远,停下时,我向外看,竟不认得这是哪儿。 内侍将我引进殿内,寥寥几盏烛火勾勒出黑暗中一个男子的身影,我迟疑着喊道:“陛下?” 他从黑暗中走出来,昏暗的灯光映出他半边身子,我对上他的视线,他的眸中好似有化不开的浓墨,不带任何温度的眼神锁在我身上,我悚然一惊。 我强自镇定,微笑道:“陛下,怎么不多点些灯呢?” 他不说话,却走到我身边来,捏住我的手腕,转身往里走。 “你来。” 我被他连拖带拽进了里间。 里间的正中央挂着的,是姐姐的画像。 烟紫色的衣裙,发髻上,是一只淡雅的莲花簪子。 与我现在身上穿的一般无二。 我转头看着陛下,他抬起手,将他手里的莲花簪子插进我的发髻。 画中人,画前人。 孰真?孰假? 陛下将头靠在我的肩上,毒蛇吐信般的呼吸打在我的脖颈处,我瑟瑟发抖时听见他森然道:“你在害怕啊?” 一室昏暗,眼前人既熟悉又陌生,铺天盖地的恐慌笼罩了我。 我霍然转身往殿外跑,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跑,只是凭着骨子里的本能和直觉。 脚踝被什么坚硬的东西狠狠打中,我重重地摔倒在地。 陛下紧紧扣住我的脚腕,将我往回拖,口中却似情人间温柔缱绻一般喃喃:“若清,你要去哪里?” 订阅解锁TA的全部专属内容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ingchunhuaa.com/ychpz/11246.html
- 上一篇文章: 故宫晒出赏花图爱卿快来陪朕赏花中国青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