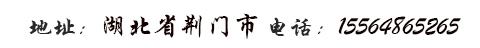原创散文回不去的故乡
|
望着窗外的濛濛细雨,借着故乡河边那几棵袅袅婷婷的垂柳,思绪,沿着长满嫩绿的小径,在如诗如画的故乡田野上,让柳笛悠扬,唱一支关于故乡的歌曲。 大伯家高高的土窑顶上的迎春花,舒展着柔软的纤腰,举着嫩黄的小喇叭,伴着轻软的春风,悠悠地吹奏着。 院子里的石碾,拖着笨重的躯体,呼呼地打着转。碾下面平躺着圆乎乎的菜籽饼,一群灰色的鸽子,咕咕咕地蹦跳着,不时用长长的细嘴,啄着越来越碎的饼渣。 屋子里的大伯错落有致地摁着榨油机长长的柄干,铜锣似的油饼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哗啦哗啦地淌着黄色的液体,像小溪一样沿着长长的堤岸,汇进地面上胖胖的油桶里。 十里八乡的三餐烟火里,飘荡的都是大伯家菜籽油的气息。 田间地头,黑油油的菜籽饼肥沃着农民的希望。 邻家后院墙头上开满了鲜红的石榴花,成群结队的蝶儿和蜂儿在花丛里嗡嗡嗡地哼唱着。密密匝匝的石榴花咧着厚厚的大嘴,让蜂儿尽情地吮吸着它们鹅黄的花蕊。 邻家院里的拖拉机里,躺满了圆滚滚的西瓜,一双双结满老茧的双手拍着,捡着,抱着,装着,四周的编织袋鼓起来了,瘸着伤腿的邻家哥哥笑盈盈地过着磅,一手收着钱,一手还不忘再抱个西瓜放进乡亲们的手里。 玉米地里,累了的村民们吃着甜甜的西瓜,热风里传播着夸赞邻家哥的话语。 厚重的露水打湿了鸟的翅膀,一人宽的小路上,蟋蟀在蒿草里喑哑地独奏着,满是沧桑,娘挑着摆满了玉米棒的担子,摇摇晃晃地移动着。 苞谷山在院里堆砌着,羸弱年迈的爷爷在屋里哭闹着,娘顾不得擦拭汗珠,洗手和面,洁白的大面片在案板上跳跃着,吞着酸香柔和的一大盆面叶,爷爷的脸上盛开了菊花。 后来爷爷走了,常年在外工作的父亲回来,看到瘦削的娘,忍不住说“这个家,幸亏有你撑着。” 娘继续着她的操劳。 洁白的雪花棉被铺满了田野,朝朝暮暮飞翔在北方天空里的小麻雀依然叽叽喳喳地谈笑着。洗过澡的雪菜,白菜,萝卜叶横躺在院里支着的干净竹笆上,一只健壮的山羊偷偷跑过去,张大嘴巴啃下去,“这是做酸菜的,可不是给你吃的。”三叔一把抓住羊脖子上的绳子,山羊撒娇地咩咩咩叫着。 记忆里,只有岁末,三叔才会在家里安稳度日,其它的时光,都是在砖窑厂里忙活。 年来了,我家的厨房里飘着和三叔家一样的酸菜羊肉汤的味道。 故乡在岁月的四季里老去,美妙的故乡,没了小河的滋润,已老态龙钟。 执笔时,辛苦一生的大伯和三叔已沉睡在故乡的田野里,厚道的邻家哥哥住进了监狱,勤劳的娘得了脑栓塞,摇摇晃晃的身体让一生坚强的她整日满脸愁绪。 故乡再也不是年轻的模样了。 唤一声故乡,泪落千行。 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的故乡……柳笛生满春的光,吹响。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ingchunhuaa.com/ychpz/11385.html
- 上一篇文章: 华春莹曾经的校园迎春花,她是中国的外交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