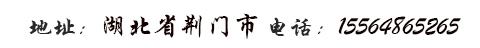史小军王舒欣论金瓶梅词话的药物叙
|
北京什么医院治白癜风比较出名 htt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药物叙事在世情小说《金瓶梅词话》中占据较大的分量,全书近一半的章回中都有叙写药物名称及用药过程之处;曲词中频繁出现的中药材将药性寒凉与西门家族的繁华热闹相映衬,展现了小说冷热对照的叙事格调。药物叙事的主要文学功能包括串联人物关系、编织小说结构,塑造医患群像、展现人情世态,暴露社会丑恶、深化小说主旨三个方面。讽喻手法的频繁出现使文本的修辞美学特征更为明显,也使小说的写作意图更加鲜明。[关键词]《金瓶梅词话》药物叙事修辞《金瓶梅词话》作为一部针砭时弊的世情小说,作者在叙事中精心构建了一个由疾病、患者和医者组成的世界。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对文本中的医家与疾病多有论述,然而,对与医疗息息相关的治病之药却留意较少,对药物的论述多聚焦在药方或单纯的药理药性之上,对药物叙事的综合研究尚显不足。因此,本文拟在整理全书药物种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药物叙事的文学功能与修辞特征,借此窥探《金瓶梅词话》的创作主旨以及世情小说的发展进程。 一、药物叙事的文本概况 (一)药物的数量、药理及用途据笔者统计,《金瓶梅词话》中提到药物之处多达次,回《金瓶梅词话》中叙写药物名称及用药过程之处有45回,占全部章节的45%。 作为长篇世情小说鼻祖,词话本中所写真实的药物多达68种: 砒霜(人言)、艾草、沉香、白蜡、水银、胡椒、百草霜、金灯花、玉马樱、金雀藤、瑞香花、十姊妹、金雀花、鹅毛菊、望江南、枸杞、迎春花、蔷薇花、玉簪花、红娘子、桃花、金盏草、红花、紫草、转枝莲、石榴花、丁香花、茉莉、黄柏、知母、地黄、黄芩、三七、木樨、玫瑰、紫河车、白鸡冠花、棕灰、牛乳、薄荷、金银花、朱砂、金箔、牛膝、蟹瓜、甘遂、定磁、大戟、芫花、斑?、赭石、碙砂、芒硝、桃仁、通草、麝香、凌霄花、葱白、蜂蜜、甘草、藜芦、巴豆、半夏、乌头、杏仁、天麻、牛黄、人乳。 以上所列药物,有20种在文中所提到的用处与现实情况相符,以李瓶儿使用的三七为例: 李时珍在万历六年至万历十六年间著成的《本草纲目》中记载,三七“生广西南丹诸州番峒深山中……此药近时始出”。[①] 《金瓶梅》中也描述花大舅“过世公公老爷,在广南镇守,带的那三七药”。[②] 可见,三七约于明中期万历年间出现,小说中三七的出产地点也与药书相符,证实《金瓶梅》的写作时间与《本草纲目》的问世应处于相近时代。 《本草纲目》 第十六回李瓶儿把价格高昂的沉香、白蜡、水银和胡椒当作货物托付给西门庆,与明代真实社会状况相吻合;第七十五回孟玉楼吃牛黄丸以及第七十九回提及的人乳等,也是时人常用药。 第七十九回中,西门庆向如意儿讨要人乳,以人乳配合服药。 明谢肇淛《五杂俎·人部一》记载,穰城(今河南邓县)有位长寿者,“不复食谷,惟饮曾孙妇乳”。[③] 大概服乳长寿之传闻,是明代流行以人乳进补的原因之一。 而人乳补脾益肾之功效,也更适合恣情纵欲的西门庆服用,与第六十七回应伯爵喝“酥油白糖熬的牛奶子”对照,牛乳亦可“补虚羸,止渴。养心肺,解热毒,润皮肤”,[④]同样是时人流行的进补方式。 另外,《金瓶梅》作为优秀的世情小说,在情节设置中有14种药物用于医家治病救人,药性与病理丝丝入扣。 如任医官于第五十五回中诊治李瓶儿时所用黄柏、知母、地黄、黄芩,均为清火止血之药,与李瓶儿产后之症对合。 《本草纲目》:“知母佐黄檗,滋阴降火,有金水相生之义。黄檗无知母,犹水母之无虾也。”[⑤] 情节中设置黄柏与知母同用,与医道完全符合,证明作者医理精湛,药物信手拈来便成章法。 《金瓶梅》第六十二回中提到三七,用来治疗李瓶儿“崩漏之疾”,《本草纲目》有证,三七(主治)“崩中经水不止,产后恶血不下”,[⑥]是切合实际的对症之药。 胡大尹为李瓶儿寻的药方白鸡冠花与棕灰,有止血效用,棕灰散治妇人“崩漏下血”,[⑦]白鸡冠花可止肠风血热,治妇人“崩中赤白带下”,[⑧]都是明代治妇人失血的验方。 另有一些文中没有直接说明药物成分的中成药,如第六十七回任医官给西门庆的百补延龄丹,《丹溪先生心法》卷三“补损部”有“延龄丹”的记述,主治“脾肾不足,真气伤惫,肢节困倦,举动乏力,怠惰嗜卧,面无润泽,不思饮食……其功不可具述”。[⑨] 第七十五回孟玉楼心口疼痛,吃广东牛黄清心蜡丸,第七十六回腹痛吃暖宫丸,此药见于明代王肯堂的《证治准绳·女科》以及《妇人大全良方》《仁裔直接》。[⑩] 《金瓶梅》诊脉开方的成药品种十分丰富,药方中有相当多的部分在中医典籍有记载,书中提到的中医学科涉及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多个学科。 《金瓶梅》对人物病情的描述与药物的使用相当详细备尽。 第五十九回潘金莲蓄意以猫扑人使官哥惊风,“搐的两只眼直往上吊,通不见黑眼睛珠儿,口中白沫流出,吚吚犹如小鸡叫,手足皆动”。[11] 而与之相比较,宋代医书《幼幼新书》载《小儿初受惊风候歌》中小儿惊风的症状如下: “小儿如得惊风候,指甲青兼黑似烟,口吐白虫便黑血,眼开不闭半抬肩,咬人白日多惊汗,忽作鸦声不可看。”[12] 官哥口吐白沫、吊眼以及声音情态都与医书相同,显见是惊风无疑。刘婆为治疗熬制灯芯薄荷金银汤,又以金箔丸研化灌下。 这里灯心薄荷汤主治心烦失眠,金箔丸中的金箔可以“疗惊痫风热肝胆之病”,[13] 宋代医师刘昉记载有“金箔镇心圆”,“治小儿一切惊气,夜睡不稳,喉中涎声,梦中狂叫,精神躁闷,并宜服之”。[14] 对症下药并无讹误,应当说,到这里刘婆的表现都没有什么问题,医院的高明医术,但也至少展现出了一个医生的基本合格素养。 而后刘婆失手,艾炙无效反而使官哥转为了慢风,西门庆请小儿科太医来看,也并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用接鼻散试之,“若吹在鼻孔内打喷?,还看得;若无喷?出来,则看阴骘守他罢了”。[15] 这里的接鼻散,较少为人所留意,但也是当时儿科所用验方。 《幼幼新书》卷十引《茅先生方》详细描述了治疗慢惊风中的药物搐鼻散,即小说中的接鼻散,处方为“瓜蒂一钱,细辛半钱”,制法“右为末”,功能主治小儿惊风四十八候。 每“用半字吹入鼻中,打喷嚏,候眼开,便将大青丹取下积热,并下惊涎后调气。”[16] 小说中的药物用法与医书中记载完全相同,主治病症也契合。 在官哥之死情节中,有着几乎完全贴近生活的真实病症与真实药物,这些药物真实地反映了明代社会生活,也使叙事变得更加合乎情理。 作者的叙述植根于明代社会生活,这种叙述的真实性有着浓厚的现实主义观感。 再配合恰到好处的叙事结构,以这样的真实引领读者走进虚构的生活氛围中,平添不少直面死亡的沉重感。 《重刻幼幼新书序》 (二)曲词中的中药材《金瓶梅》中所统计68种药物,都属于传统中医所用药材。 文本中的中药材不仅体现在一般的叙事情节中,也展现在曲词中。 《金瓶梅》中曲词较多,其中有四个曲词涉及中药材,较为典型的是第三十三回潘金莲罚陈经济唱《山坡羊》: “我听见金雀儿花眼前高哨,撇的我鹅毛菊在斑竹帘儿下乔叫。 多亏了二位灵鹊儿报喜,我说是谁来,不想是望江南儿来到。 我在水红花儿下梳妆未了,狗奶子花迎着门子去咬。 我暗使着迎春花儿绕到处寻你,手搭伏蔷薇花口吐丁香把我玉簪儿来叫。 红娘子花儿慢慢把你接进房中来呵,同在碧桃花下斗了回百草。 得了手我把金盏儿花丢了,曾在转枝莲下缠勾你几遭。 叫了你声娇滴滴石榴花儿你试听知,被九花丫头传与十姊妹什么张致?可不教人家笑话不了。”[17] 整首曲词由花名构成,风格活泼新鲜。 首先,花名可喻动物,如“金雀儿花”喻“金雀儿”叫,“狗奶子花”象征“狗”“迎着门子去咬”,生动形象且富有趣味。 其次,花名可喻人物,一语双关,如“迎春花儿”可指迎春花,又可指李瓶儿的侍女迎春;“玉簪儿”指玉簪花,李衙内的妾也叫玉簪儿。 值得注意的是,曲词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称指代“望江南儿”,应作名词解。 望江南并不是花名或动物名,但其他人称都以植物作代,望江南若以曲牌名解释,则于理不通,因此它应当是豆科决明属植物望江南,也是时人所熟知的一种中药,《药性论》《开宝本草》与《本草纲目》中都有记载。 在密集的花名中间穿插一种中药,显得格外突兀,难道是作者已经绞尽脑汁,却并没有其他种类的花可以用来安插在曲词中,只能用中药来填补空缺了吗?显然并不可能。 那么是否为作者刻意留的一个破绽?中药非花,但若将所有的花名都看作中药,疑惑则可迎刃而解。 事实也确实如此。金雀花:“能透发痘疮……解毒攻邪。”[18]鹅毛菊:菊花。 疏散风热、清肝明目、清热解毒。望江南:“清肝明目,健胃润肠……解毒。”[19] 狗奶子:枸杞。[20]性微寒,枸杞苗“消热毒,散疮肿”。[21] 迎春花:解毒,“治肿毒恶疮”。[22]蔷薇花:清暑解毒,“可罨金疮”。[23] 丁香花(雌丁香):主治“风水毒肿,霍乱心痛,去恶气”。[24] 玉簪花:“甘、辛,寒,有毒。捣汁服,解一切毒,下骨哽,涂痈肿。”[25] 红娘子:即樗鸡。[26]有小毒,破瘀,散,攻毒,“主瘰疬”。[27] 桃花:治心腹痛及秃疮、头上肥疮、手足瘑疮。[28] 金盏草:长春花。酸、寒,治“肠痔下血久不止”。[29] 红花:活血,解痘毒,散赤肿。[30]转枝莲:祛风除湿,活血止痛。[31] 石榴花:凉性,解毒,治“九窍出血”。[32] 十姊妹:又名佛见笑,清热化湿,“治伤寒危笃立效”。[33] 《本经逢原》 可见,曲词中所有的花表面上看上去是给文辞增加艳色,实质上在文中以中药的性质出现才能达到文意的和谐统一。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15种中药,药性与功用惊人地相似,都作清心解毒之用。 这种现象很难用巧合来解释,但强行进一步深入阐释,又有过于穿凿之嫌。 不妨比较一下小说文本中出现过的其他花及其药性。以花入膳在《金瓶梅》中是常事,饮食中常见花以木樨、玫瑰为例(玉米面玫瑰果馅蒸饼儿)。 木樨:桂花。甘、辛,大热,温中,坚筋骨,通血脉……补命门不足,益火消阴。[34] 玫瑰:气香性温,味甘微苦,入脾,肝经,和血行血。[35] 可以看出,同样是花,曲词中的药性凉解毒,而饮食用花药性却甘热。 除花之外,膳食中包括牛乳、人乳以及西门庆常吃的鸽子雏儿等等,无一不是味甘性热的滋补佳肴,大热之性对比下,愈发衬得曲词中的中药药性格外寒凉。 膳食辛热温补的作用,的确适合滋补养身,但西门庆狂欢纵欲热度不减,以中医医理来看,未免火热淤积,病邪上攻,郁结成毒。 小说中连应伯爵也看不下去,劝西门庆:“你这胖大身子,日逐吃了这等厚味,岂无痰火?”[36] 作者以人乳等补品预先埋伏下西门庆的死因。 《本草纲目》说人乳“有饮食之毒,七情之火也。”[37] 这与西门庆临终前“下卵肿毒”的现象——“太极邪火,聚于欲海”[38]的诊断正好相符,西门庆之死的表象病理明显是热毒无处泄泻,根本原因是耽于自身纵情声色,药石回天无力。 这时我们再折返至第三十三回看曲词中药的寒凉之性与解毒之功效,更像是作者一片苦心,预先伏线千里,是对文中人物的告诫与警醒。 《金瓶梅》全文中着力写病亡三人,即官哥、李瓶儿和西门庆,官哥病时有朱砂丸、灯心薄荷汤等治惊风的药,李瓶儿病时有归脾汤、三七等止血之方, 然而全文最重要的男主角西门庆,应是着墨最多之人,却竟然从病到亡,在叙事中并无一个药方出现,仅都是以“抓了些药”这样敷衍的手法匆匆带过,似乎不合情理。 曲词里出现的多种药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这种疑惑。 学界已有共识,冷热对照是《金瓶梅》的叙事格调。 西门家族沉迷于娱乐纵情于声色,以追求“真乐”“快活”为人生目标,作者以此致力于展现扭曲、黑暗、病态的社会。 病者自有医家对症下药,然而病态的社会又用什么医疗?在《金瓶梅》曲词中的中药里似乎也能找到答案。 西门家族看似一团“热腾腾”,人生得意时花团锦簇,有烈火烹油般的繁华风流;园中常见观赏植物与之相衬,也艳丽多姿,一派富贵景象。 如第十九回中花园赞词:“木香棚与荼蘼架相连,千叶桃与三春柳作对。也有那紫丁香、玉马樱、[39]金雀藤、黄刺薇、香茉莉、[40]瑞仙花。[41]” 然而这些植物美则美矣,却也几乎都是寒凉之物,均有解毒清火的效用。 张竹坡所谓冷热金针之法,即既有一热,必有冷针锋相对,“夫一部《金瓶梅》,总是冷热二字,而厌说韶华,无奈穷愁,又作者与今古有心人,同困此冷热中之苦”。[42] 世情人情概不例外,药性亦如此。这里的药物,可清书中人物永不止息追逐欲望之火,解社会污浊风气所引病邪之毒。 药性的冷与环境的热集中在一起展示,热闹中渗透着清冷。冷与热的互渗形成了浑然一体的戏剧性对比,从中呈现出家族的兴衰和社会的变迁。 《竹坡闲话》书影 二、药物叙事的文学功能 《金瓶梅词话》中直接描写药物的情节较少。 全书中的药物叙事主要源于医者与病者之间的互动,或家族内外人情往来之间的交流,可以说大量的用药情节是药物叙事的核心内容。 药物情节主要分布在第四十九回到第七十九回之间,即官哥、李瓶儿、西门庆三人死亡的情节,是全文药物频率出现最密集的章回。 小说中的主角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等人都或多或少地服食过不同的药物,各种不同类型的药物交叉作用于人物身上,起到串联整体叙事构造的作用。 (一)编织小说结构,串联人物关系 首先,药物是小说中无法忽视的一个结构性要素。 小说主角西门庆从出场便经营着一家生药铺,由此开始,药物勾勒出五条互相交错的线索: 西门庆由卖药发家,借毒药杀人,因春药纵欲,吃补药延寿,最后又死于医药。 从生至死,一生与药息息相关不可分割,每一种药都不是孤立存在于西门庆的生活中,而是互相影响产生新的意义。 西门庆服用春药纵欲伤身,因此用补药平和养生;使用毒药害人性命时冷酷无情,自己生病时又遍寻医药救人性命。 实质上,这些药物在文本表层意义上看似性质完全不同,药物叙事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最终殊途同归,全部成为了西门庆丧命的催化剂。 再看李瓶儿出场时,说丈夫花子虚在外胡行,为此“气了一身病痛在这里”,[43]暗示情欲得不到满足,需要精神上的“药”来医治。 为了表达对西门庆的一片痴心,交给西门庆贵重的药物沉香、白蜡、水银和胡椒。 而后又因孤枕难眠,得了梦交之症靠蒋竹山治疗才能康复;嫁入西门家族后,李瓶儿又靠西门庆这种“药”治疗情欲才能活命,但她同时又是西门庆泄欲的牺牲品,暗示了李瓶儿必死的结局。 西门庆与李瓶儿二人都试图通过药物获得更好的“生”,却反被药控制导致死亡,这种由生到死的变化巧妙地完成了药物叙事情节的循环闭合,与作者所点明的“天道循环”主旨相呼应。 其次,不同人物使用药物的交集也会碰撞出情节上的火花,作为叙事暗线埋下伏笔,引出主旨。 吴月娘为了求子使用坐胎药,潘金莲也因使用坐胎药而与吴月娘大吵,这里引起的冲突是文章叙事一大转折, 此前家庭中暗流涌动,表面上却是一团和气,从坐胎药事件后,勾心斗角的算计暴露于人前,为潘金莲被月娘赶出家门埋下伏笔。 另外,当吴月娘使用坐胎药时,西门庆偏偏为了讨好吴月娘使用春药。 这也使吴月娘产生一种必定有子的预感,“他有胡僧的法术,我有姑子的仙丹,想必有些好消息也”。[44] 需要注意的是,赠春药的胡僧和赠坐胎药的薛姑子在小说当中从来没有碰过面,二人留下的药物都是世间遍寻不到的方药,在壬子日当天的同一叙事时空借西门庆和吴月娘交汇在一起,也为后续情节埋下伏笔。 僧尼作为世外之人,代表佛家解脱轮回万法皆空的世界观,因此,胡僧赠送给西门庆的春药和薛姑子的求子药融汇在一处时,结胎生下的孝哥这一人物有着浓厚的宗教象征意义,是全然虚幻的存在。 因此,孝哥天然具有与尘缘无关的出世性质,并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入世的凡人继承吴月娘的家业。 接下来,这个因药幻生的人物又承担了揭示真相的叙事功能,第一百回显示,睡在床的孝哥原是披枷带锁的西门庆转世,可见,吃药生子原是痴心妄想。 作者设置这一段药物情节的主要目的就是点明六道轮回、因果循环的主旨,从而起到勘破世情、劝示读者的作用。 万历本 (二)塑造医患群像,展示人情世态 《金瓶梅》中的药物叙事,也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医患形象的丰富性。 书中花子虚患有伤寒,官哥受惊,李瓶儿气血两虚,西门庆肾气衰竭,春梅贪淫骨痨等,病症五花八门,病情或轻或重。 以书中道德视角批判,西门庆等人或死有余辜,但书中没有一人所患之病为不治绝症,只要方法得当,都可以治愈。 因此他们最后纷纷死亡的结局,就直接原因来看,是死于庸医之手。庸医是杀人的凶手,庸医所开出的药物正是杀死病人的凶器。 下面试以李瓶儿之死为例说明。 医师中唯一看似稳重可靠的任太医,却也间接将李瓶儿送上黄泉路。 官哥死后,李瓶儿怀着失子之痛,又经潘金莲每日喝骂,“把旧时病症,又发起来,照旧下边经水淋漓不止。 西门庆请任医官来看一遍,讨将药来,吃下去如水浇石一般,越吃药越旺。 那消半月之间,渐渐容颜顿减,肌肤消瘦,而精彩丰标无复昔时之态矣”。[45] 李瓶儿曾吃任医官药极有效果,为何如今却不见效应了,反而越吃越重? 最后一个阶段李瓶儿下血不止时,任医官治疗李瓶儿时说: “老夫人脉息,比前番甚加沉重些。七情感伤,肝火太盛,以致木旺土虚,血热妄行,犹如山崩而不能节制……若所下的血,紫者犹可以调理,若鲜红者,乃新血也。学生撮过药来,若稍止则可有望,不然难为矣!”[46] 乍一看,任医官称李瓶儿血热妄行,肝火太盛,以病因而论头头是道,亦有医书可证明。 医科典籍中称“女子之性执拗偏急,忿怒妒忌以伤肝气。肝为血海,冲任之系,冲任失守,血气妄行也”。[47]看上去合情合理。 但在明清医学资料中,可以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与小说中的疾病情节对照。 晚明时期医学名家傅山所著的《傅青主医学全书》中有一段疾病症状恰巧与李瓶儿之病极其相似,可供参考比对。现摘录如下: “妇人有经水过多,行后复行,面色萎黄,身体倦怠,而困乏愈甚者,人以为血热有余之故,谁知是血虚而不归经乎! 夫血旺始经多,血虚当经缩,今曰血虚而反经多,是何言与?殊不知血归于经,虽旺而经亦不多;血不归经,虽衰而经亦不少。 世之人见经水过多,谓是血之旺也,此治之所以多错耳。”[48] 这段话从根本上推翻了任太医的诊断结果,依此来看,李瓶儿并不是血热,而是血虚之症,任太医不仅不能治病,所下之药反而害人不浅。 李瓶儿在任太医诊治之前,形态是“下边似尿也一般只顾流起来,登时流的眼黑了……忽然一阵旋晕的,向前一头拾倒在地”。[49] 《傅青主女科》中有“妇人有一时血崩,两目黑暗,昏晕在地,不省人事者,人莫不谓火盛动血也。然此火非实火,乃虚火耳”。[50] 两相对照,李瓶儿明显完全贴合血虚的症状。此外,在小说的治疗过程中,任太医认为,紫血可治愈,红血则无药可治。 《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中则称“经水过多,清稀浅红,乃气虚不能摄血也。若稠粘深红,则为热盛有余”。[51] 可见,李瓶儿当为血虚之症无误,任太医做出的血热诊断是完全错误的。血虚导致的下血之症,似乎完全不在任太医的医疗知识范围内。[52] 故李瓶儿吃了任太医治疗血热的药,“其血越流之不止”,病情日益加重。 整部《金瓶梅》的医生中,任医官已是公认最端庄持重之人,连任医官诊病都如此稀里糊涂,其他医生自不待言。 刘婆失手治死官哥,使李瓶儿眼睁睁看着儿子搐死在自己怀里导致身心俱损;赵龙岗的自我夸耀与他开出荒谬绝伦的处方相映成趣,全面立体式地展现出一个不学无术的骗子形象; 胡太医治疗病人医术毫不见效,反倒擅长配置害人性命的堕胎药,还振振有词地称“天地之间,以好生为本”,言辞之虚伪与态度之做作实在忍不住令人发噱。一部书“骂尽诸色”,又令人可叹。 李瓶儿曾坚信医生的职业道德,替这些丑态百出的医生辩解,“孝顺是医家,他也巴不得要好哩”。[53] 然而李瓶儿高估了《金瓶梅》中所有医生的良知与技能,有着职业道德的任太医,尚且因无心误诊而断送了她的性命,那些走街串巷满嘴胡言的巫医与神棍们将如何对待病人更可想而知。 这些荒唐可笑且使人警醒的对比,尖锐而深刻地揭露了草菅人命的庸医的危害。 《傅青主女科》 (三)暴露社会丑恶,深化小说主旨《金瓶梅》不遗余力对用药情节的大书特书,使药物叙事成为一条贯穿全文的主线。 值得注意的是,文本中出现的第一种药物便是毒性剧烈的砒霜。 实质上,以《金瓶梅》构思之精妙,布局之细密,我们对文中出现的第一种药物不可以等闲视之。 砒霜作为毒药,足以奠定全文药物的主要内涵,即《金瓶梅》中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药物,几乎都是要命之药,没有一种真能治好病,使人健康安乐。 这种设定与世俗意义上的药物价值背道而驰,却也正是《金瓶梅》劝世主旨展现的一种具体形态。 首先,《金瓶梅》中叙写药物形象地暴露了社会黑暗及其无药可治的现实,因此在药物叙事中,倾向于对丑恶欲望的极度摹写。 第一,药物外形丑陋。《金瓶梅》中胡僧传药时对春药外形的描写:“形如鸡卵,色似鹅黄……外视轻如粪土,内觑贵乎玕琅。”[54] 丑陋到如粪土般被轻视的药物外形,使人一见便想敬而远之,但西门庆却丝毫不觉,满心欢喜以为得到至宝,自此走上荒淫恣肆的道路,因此,药物的审丑意象包含西门庆纵欲罪恶的意义。 第二,药物气味恶劣。 《金瓶梅》中吴月娘在求子使用坐胎药时,服下头胎衣胞,“虽则是做成末子,然终觉有些生疑,有些焦剌剌的气子难吃下口……先将符药一把罨在口内,急把酒来大呷半碗,几乎呕将出来,眼都忍红了,又连忙把酒过下去。喉舌间只觉有些腻格格的。”[55] 其味经作者描述实在腥恶难闻,令人几欲作呕。 这里的头胎衣胞即人体胎盘,在中药中可称为紫河车,确实是有滋阴补阳的效用,也可用来治疗不孕症。 然而自汉代开始,民间便流传丢失损毁胎盘对新生儿不利的说法,尤其忌讳为人食之。 唐代崔行功在《小儿方》曾云: “胞衣宜藏天德月德吉方,深埋紧筑。若为猪、狗食,令儿颠狂;蝼蚁食,令儿疮癣;鸟鹊食,令儿恶死;弃火中,令儿疮烂;近社庙、井、灶、街巷,皆有所忌。”[56] 自唐至清,历代都有医者反对以胎盘入药,更普遍的做法是埋于地下。 清代张秉成在《本草便读》中称:“小儿之胞衣,宜藏安妥之处,或深埋紧筑,令儿长寿。若为虫蚁所食,儿即有病。”[57] 因此吴月娘食用他人胎盘,于习俗而言是非常明显地损人肥己的行为,这与她素日展现出厚道大方的形象背道而驰,在这里,作者通过隐笔展现出月娘的道德缺陷与人性之恶。 第三,药物毒性猛烈。 《金瓶梅》第五十四回胡僧传西门庆药物时,明白地告诉他药物的毒性猛烈程度: “恐君如不信,拌饭与猫尝。三日淫无度,四日热难当,白猫变为黑,尿粪俱停亡。夏日当风卧,冬天水里藏。若还不解泄,毛脱尽精光。”[58] 以此警告西门庆不可纵欲过度。 然而西门庆为了服药后寻欢作乐抛弃了胡僧的劝解,沉溺于肉欲不能自拔,以此突出《金瓶梅》中的纵欲内涵。 明代中后期,国家政治腐败,皇帝昏乱荒淫,沉迷方术,朝野上下多向皇帝进贡各类性药或长生不老药,以此希获圣宠。 上行下效,于是社会风气日益腐化堕落,人欲泛滥的思想风靡一时,各类性药借此精神土壤而蓬勃发展开来。 西门庆借药纵欲淫乱无度,正是当时市井民间人欲泛滥现象的剪影,药物意象浸透着时代风气的污浊与糜烂。 其次,是以药物极写人性之恶自私自利,刻画凉薄世态。 潘金莲为了追逐欲望,不惜以药谋杀相随多年的亲夫,又为了欲望,毫不体恤病中的西门庆,以春药送了他性命; 潘金莲与陈经济偷情怀孕后做出吃下堕胎药的决定时完全秉持着维护自身现有利益的原则,作者没有分出一丝笔墨描绘她是否对腹中掉下的骨肉有所牵挂; 陈经济每每借取药为由与潘金莲偷情,又在道观中吃黄酒做的“毒药汁”,将清规戒律抛诸脑后,与娼暗通奸犯案吓死了任道士; 庞春梅在嫁入守备府后乔张做致,做出许多病态吃药,目的是为了与陈经济偷欢。 《金瓶梅》中的药物是一切欲望实现前的铺垫,又在细枝末节处借药物情节为引,为纵欲狂欢推波助澜。 在西门家族中,如果从药物角度来观察人物的生理与心理状况,会发现除了官哥病重时李瓶儿因母爱产生的本能焦灼外, 全文几乎看不到真正因病吃药而体现的人性关怀,只是以药物之丑影射人性之丑,进而给读者展示了享乐、纵欲、拜金思想所构建的黑暗世界一角,人人都在食色财气的狂欢中迷失,走向自我欲望的膨胀与毁灭之路。 《本草便读》 三、药物叙事的讽喻修辞特征 修辞是文学作品在写作过程中一道不可或缺的加工流程。修辞使文本内容富有文学美感,也使文章立意更加鲜明。 《金瓶梅》中的修辞形式使药物叙事更加有针对性和指向性,在药物叙事中,讽喻世情,揭穿世人真面目的意味体现得格外明显。 第一层面,通过药物药性与人物行为之间的悖论,起到反讽作用。 作者将药物与各类人物言行联结在一起,形成极不协调的叙事语境,以此生发出讽刺效果。 (一)春药与毒药 文本中的药物,首次出现是在第五回,即潘金莲用西门庆赠予的砒霜毒杀武大郎。 本来潘金莲对与西门庆偷情行为已经感到满足,并没有杀掉武大郎的念头,在武大郎被踢伤后,她也只指望武大郎自死。 然而在王婆和西门庆的怂恿下,她下毒杀夫,又千方百计地嫁入西门家,踏上了疯狂追逐欲望的道路。 自毒杀武大郎后,潘金莲的人性之恶被彻底激发,这也是小说中人性之恶通过药物首次展现出来。 毒杀武大郎这桩案件并未随着武大郎死去而湮没,而是作为一根暗线潜伏在文章中,一次又一次地被人提起,使做了亏心事的潘金莲与西门庆不得安宁。 更离奇的是,每一次文中出现毒药,都有人间接地因此死亡。 第一个提及毒药的人是孙雪娥,第十一回她背地里对吴月娘和李娇儿说潘金莲“当初在家,把亲汉子用毒药摆死了,跟了来”。[59] 由此二人结下深仇。后春梅为了替潘金莲报复孙雪娥,将其变卖为娼,导致孙雪娥上吊身亡。 第二十五回中,西门庆因来旺儿得知了潘金莲毒药杀夫之事,将其发配徐州,来旺儿的妻子蕙莲因此上吊。 第八十七回,武松归来后又一次翻出砒霜旧事,手刃潘金莲。 全文看似被毒杀者只有武大郎一人,但文本中共有四次提及毒药,有四人因此而死,可以说每一次毒药出场,都是人物死亡的导火索。 《金瓶梅》开场就以砒霜这种毒性剧烈的药物奠基,讽刺书中糜烂的狂欢生活就像砒霜一样有着剧毒,人物浸淫日久而不觉其害,因此大多都不得善终。 看似无害的春药,同样起到了毒药的效用。 小说第四十九回,西门庆得到了胡僧所传春药,就此进入了纵欲享乐的极乐世界,仅文中所描写西门庆使用春药的段落就有十余次,忘乎所以因此亡身。 此外,潘金莲喂服西门庆过量的春药,亦曾强灌武大郎砒霜,直接将二人性命断送在其手上。 第一次谋杀亲夫与第二次害死西门庆的情节何其相似,可见,春药也是实质意义上的毒药,作者有意设置潘金莲杀夫的雷同情节,使读者将二者联系起来,春药与毒药的隐喻关系从而凸显。 值得注意的是,潘金莲是文本中唯一将春药和毒药二者特性合二为一的标志性人物。 以男性视角观察,潘金莲风流婉转令人销魂蚀骨的媚态定是春药无疑,但其自私冷漠又刁恶凶狠的性格亦是剧毒不可沾染。 作者不遗余力地反复描绘潘金莲的美貌与狠毒,时时提醒读者贪恋色欲易亡身、不可不慎的主旨,再一次点明色空观念,达到警醒世人的目的。 另一个死于“春药”的人是李瓶儿。 李瓶儿的死因表象是庸医杀人,而张竹坡点出深层原因,胡僧施药“盖为死瓶儿、西门之根”。[60] 整部小说中,只有蒋竹山在第十七回曾治好过李瓶儿肉体的病,然而仅仅肉体健康不能使她满足,因此李瓶儿为西门庆抛弃蒋竹山,“蒋竹山者,又将逐散也”。[61] 象征她放弃了健康正常的生活转而追逐纵欲狂欢的世界,蒋竹山在她的眼里,确实只是一个治疗躯体病痛的医生,根本不能作为丈夫看待,“是个中看不中吃蜡枪头”,[62]因此她才口口声声地对西门庆表白“你是医奴的药一般”。[63] 张竹坡评价瓶儿是痴人,她的“痴”,集中体现于对病态情欲的执着追逐,对治疗疾病的医药视而不见,却对害人性命的毒药——纵欲狂欢甘之如饴。 《金瓶梅》第六十一回前评道: “瓶儿本是花瓶,止为西门是生药铺中人,遂成药瓶。而因之竹山亦以药投之,今又聚胡、赵、何、任诸人之药入内,宜乎丧身黄土,不能与诸花作缘也。”[64] 李瓶儿因痴生病,因药而愈又不知悔改,沉迷于肉体欲望而埋下死根,终因药而送命。 皋鹤堂本 (二)堕胎药与坐胎药求子主线最早出现于第二十一回,吴月娘烧夜香时发愿:“不拘妾等六人之中,早见嗣息,以为终身之计,乃妾之素愿也!”[65] 一个贤良大度的妇人形象自此树立起来。 然而吴月娘又在李瓶儿已经生子,西门家族有继承人的情况下通过祝祷吐露了自己的真心话:“若吴氏明日壬子日,服了薛姑子药,便得种子,承继西门香火,不使我做无祀的鬼,感谢皇天不尽了!”[66] 可见,吴月娘实际上认为只有自己亲生的儿子才能“继承西门香火”,其他妾室的儿子都不在思量范围内。 使用坐胎药的原因,主要是基于自身地位和利益的的考量,母以子贵。作者在这里大书一笔,将吴月娘温厚贤良中暗含争名夺利的心思给戳破了。 吴月娘使用坐胎药成功怀孕后,潘金莲也希望通过坐胎药获得孩子。潘金莲求子的目的与吴月娘不同,主要是为了获得宠爱,留住西门庆的心。 然而潘金莲壬子日服下药生子的计划受阻,阻碍者正是上一次使用求子药成功的既得利益者吴月娘。 这种刻意设置的差异叙事使潘金莲也因此格外记恨了一层,和正身怀有孕的吴月娘吵架时冲口而出:“像这等的却是谁浪?”“你不养下汉,谁养下汉来?”[67] 看似胡搅蛮缠,却句句暗讽吴月娘因药有子之事,而吴月娘也因心虚而大怒,两下里撕破面皮,闹得不可开交。 坐胎药的冲突标志着潘金莲使用求子药的彻底失败。潘金莲嫁入西门家后一直有着强烈的生子愿望,使尽浑身解数也未能成功。 然而在西门庆死后,她却事与愿违地怀孕了。 这个胎儿不仅不能为自己增添荣光,反而是与女婿陈经济偷情的铁证,会让她颜面尽扫,在西门家无地容身,这无疑是对潘金莲平日喜欢“掐尖儿”,争强好胜性格的一种强烈讽刺。 从小说中的现实意义去考虑,潘金莲如果不堕胎,“弄出个怪物来”,就只能是“寻了无常罢了,再休想抬头见人!”[68] 而如果想再体面地活下去,胎儿就不能留住。因此,堕胎药在这里同样有着双重反讽的性质,它既是治潘金莲“病”的药物,也是取腹中胎儿命的药物。 《金瓶梅》中的药物叙事,通常都有其两面性,治病与要命两件看似性质完全相反的事情,却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可见作者构思的奇巧之处。 第二层面,通过关于医药的趣事与笑话,在幽默中传递讽刺现实的思想。 笑话本身就有幽默夸张却反映现实的功能,因此讽喻时弊最为切当。张评本第五十四回任医官给李瓶儿看过病后,因不收诊金,西门庆讲了一个笑话: “有一人说道:‘人家猫儿若是犯了癞的病,把乌药买来煨他吃就好了。’旁边有一人问:‘若是狗儿有病,还吃甚么药?’那人应声道:‘吃白药。’吃白药,可知道白药是狗吃的哩。” 那任医官拍手大笑道:“竟不知那写白方儿的是甚么?”[69] 这是一个讽刺患者的笑话,但在文中,这个笑话起到了多重反讽的作用。 任医官在听过笑话拍手大笑的同时,又站在正统医者的角度上以良医自居,嘲笑一些不学无术的庸医开无效的药方,形成了文中对医生和患者的双重嘲讽。 然而之后任医官自身诊断错误,开出的药方有导致李瓶儿死亡的可能,因此自己也意外地被囊括进了庸医的范围,成为被嘲讽的对象, 这就使任医官对“开白方儿”医生的嘲讽显得格外荒谬可笑,呈现出了一种戏剧化的怪诞效果,也使文本外的读者从高于文本现实的视角感受到了浓厚的讽刺氛围。 除此之外,西门庆讲给潘金莲的蒋竹山看病笑话也是典型的反讽。一个人请蒋竹山看病时,蒋在街上买了一尾鱼,看病时挂在病人家的帘钩儿上。 “手把着脉,想起他鱼来……只顾且问:‘嫂子,你下边有猫儿也没有?’不想他男子汉在屋里听见了,走来采着毛,打了个臭死,药钱也没有与他,把衣服扯的稀烂,得手才跑了。”[70] 这个笑话将蒋竹山的狼狈刻画得淋漓尽致,蒋竹山先前在潘金莲眼中还是“谦恭”“文墨人儿”的端庄医者形象轰然倒塌,讽刺之意不言自明。 作者在叙述中语言简练,也无需发表评论,而是用最为直观的画面,寥寥数语,揭示出事物的本质,表现出浓重的反讽情态。 第三层面,由医药直上升至主题层面,讽喻整个社会。 小说第十七回中,宇文虚参蔡京本中提到,“譬犹病夫在此,腹心之疾已久,元气内消,风邪外入,四肢百骸,无非受病,虽卢、扁莫之能救,焉能久乎?今天下之势,正犹病夫尫羸之极矣。君,犹元首也;辅臣,犹腹心也;百官,犹四肢也”。[71] 这一段中以身体喻国家,以疾病喻奸臣,以医药比喻治理社会的运行法则。 从医药角度切入小说主题,表明国家亦犹如身体,不经治理就会病入膏肓。 从这一角度来看,“作者抱无穷冤抑,无限深痛……不得已籍小说以鸣之”。[72] 讽刺的范围扩大到最宏观的规模,对以蔡京为首的一干国家蛀虫的弹劾与指控,正是对明代中后期社会现状的控诉。 这种宏观反讽赋予了作品一种强大的暴露社会黑暗现实的力量,也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深沉责任感。 综上,从《金瓶梅词话》的药物叙事角度可以探索药物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联脉络,揭示文本中医学、文学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通过药物叙事可鉴人情世态,人物形象借此也得以丰满。同时,药物叙事也有着营造小说的结构、推动情节的发展、深化小说主旨的作用。 《金瓶梅》中讽喻的修辞形式使药物叙事更加有针对性和指向性,使文本内容富有文学美感,也使文章立意更加鲜明。 《金瓶梅》作为世情小说的先驱,能够承前启后,在包括药物叙事等许多艺术手法的表现方面都作了可贵的探索和准备。 《红楼梦》的药物叙事既受到《金瓶梅》的启发,也有对《金瓶梅》的超越,在具体的写作方式和美学旨趣上都有不同,从中以看出药物叙事在中国古典长篇世情小说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作者史小军教授 [①][明]李时珍编纂,刘衡如、刘山永校注:《新校注本本草纲目》(第4版),北京:华夏出版社,年,第页。为行文方便,《新校注本本草纲目》下文统一简称为《本草纲目》。 [②][明]兰陵笑笑生原著,梅节校订,陈诏、黄霖注释:《金瓶梅词话》,台北:里仁书局,年,第页。为行文方便,《金瓶梅词话》下文统一简称为《金瓶梅》。 [③][明]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年,第89页。[④]《本草纲目》,第页。[⑤]《本草纲目》,第页。[⑥]《本草纲目》,第页。[⑦][明]张介宾:《景岳全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年,第页。[⑧]《本草纲目》,第页。[⑨][元]朱震亨撰,[明]程充编订:《丹溪先生心法》,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⑩]李晓梅、王忠禄:《论〈金瓶梅〉中的医者叙写》,高原、朱忠元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第9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年,第59页。[11]《金瓶梅词话》,第页。[12][宋]刘昉:《幼幼新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年,第页。[13]《本草纲目》,第页。[14]《幼幼新书》,第页。[15]《金瓶梅词话》,第页。[16]《幼幼新书》,第页。[17]《金瓶梅词话》,第页。[18][清]赵学敏辑:《本草纲目拾遗》,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年,第页。[19]《全国中草药汇编》编写组编:《全国中草药汇编》(第2版)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年,第页。[20]狗奶子的含义有多种说法,《金瓶梅大辞典》中将狗奶子解释为蒲公英之俗称。《现代北京口语词典》认为狗奶子是小蘖,《本草纲目·木部》称小蘖为山石榴,“子细黑圆如牛李子及女贞子”(《本草纲目》,第页)。然而若以山东方言而论,狗奶子其意为枸杞,明晚期诗僧释函可曾作诗《狗奶子》,描述有“味酸性微寒,嘴尖腹渐大。丛生缀短枝,浑疑人血洒……陈列俎豆间,明明格上帝”([明]释函可:《千山诗集》卷三,清刻本),从味觉、药性、外形与作用来看,似乎都与枸杞更为相似。故本文取枸杞之说。[21]《本草纲目》,第页。[22][明]胡濙:《卫生易简方》,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年,第页。[23][清]汪绂撰,江凌圳等校注:《医林纂要探源》,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年,第页。[24]《本草纲目》,第页。[25]《本草纲目》,第页。[26]红娘子并非花,而是药用昆虫。见程淦藩:《红娘子考》,《昆虫知识》年第2期。[27]《本草纲目》,第页。[28]《本草纲目》,第页。[29]《本草纲目》,第-页。[30][清]张璐著,赵小青、裴晓峰校注:《本经逢原》,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年,第76页。[31]《全国中草药汇编》编写组编:《全国中草药汇编》(第2版)下,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年,第-页。[32]《本草纲目》,第页。[33]《本草纲目拾遗》,第页。[34]《本草纲目》,第页。[35]《本草纲目拾遗》,第页。[36]《金瓶梅词话》,第页。[37]《本草纲目》,第页。[38]《金瓶梅词话》,第页。[39]玉马樱(杜鹃),又称羊踯躅,主治“温疟恶毒诸痹”。见《本草纲目》,第页。[40]茉莉,“清热解表,利湿……镇痛”。见《全国中草药汇编》(第2版)下,第页。[41]瑞仙(水仙),“清热解毒,散结消肿”。见《全国中草药汇编》(第2版)下,第页。[42][明]兰陵笑笑生著,王汝梅校注:《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年,第页。[43]《金瓶梅词话》,第页。[44]《金瓶梅词话》,第页。[45]《金瓶梅词话》,第-页。[46]《金瓶梅词话》,第页。[47]张奇文主编:《妇科医籍辑要》,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年,第47页。[48]张存悌主编:《傅青主医学全书》,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年,第18页。[49]《金瓶梅词话》,第页。[50]《傅青主医学全书》,第6页。[51][清]吴谦等撰,鲁兆麟等点校:《医宗金鉴》,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年,第页。[52]任太医早在第五十四回为李瓶儿诊病时已切实诊断出李瓶儿血虚的病症,“元气原弱,产后失调,遂致血虚”。(《金瓶梅词话》,第页)第六十回作者亦明确写李瓶儿是“旧时病症,又发起来”(《金瓶梅词话》,第页),而后却错诊李瓶儿为血旺之症。[53]《金瓶梅词话》,第页。[54]《金瓶梅词话》,第页。[55]《金瓶梅词话》,第页。[56][清]汪昂编撰,余力、陈赞育校注:《本草备要》,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年,第-页。[57][清]张秉成撰著,张效霞校注:《本草便读》,北京:学苑出版社,年,第页。[58]《金瓶梅词话》,第页。[59]《金瓶梅词话》,第页。[60]《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页。[61]《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页。[62]《金瓶梅词话》,第页。[63]《金瓶梅词话》,第页。[64]《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页。[65]《金瓶梅词话》,第-页。[66]《金瓶梅词话》,第页。[67]《金瓶梅词话》,第2-3页。[68]《金瓶梅词话》,第页。[69]《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页。[70]《金瓶梅词话》,第页。[71]《金瓶梅词话》,第-页。[72]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68页。文章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学术研究》,年第3期。转发请注明出处。《金瓶梅》与名人过往 (视频制作李明) 往期推荐 史小军:论《金瓶梅》中的偷窥与窃听浦安迪(美):《金瓶梅》艺术技巧的一些探索(上)浦安迪(美):《金瓶梅》艺术技巧的一些探索(下)黄霖:“人”在《金瓶梅》中杨彬:“尊情观”与崇祯本《金瓶梅》批评许建平:《金瓶梅》中货币观念与审美价值的逻辑走向周中明:《金瓶梅》对中国小说语言艺术的发展谢尔金指点个在看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ingchunhuaa.com/ychpz/7902.html
- 上一篇文章: 从顺丰速递聊起
- 下一篇文章: 4个哑铃动作满足练臀需求,雕刻臀肌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