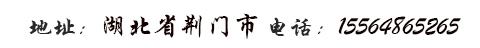韶华五月middot感恩贰
|
/无题/ 高一一班于清 悬溺沉浮 跌跌撞撞从一捧雾行至一席荒唐雾 羽翼浸染苦难的风吹拂 十万八千里路 恸失母亲的年岁里我是否有幸成为你的 救赎 抑或是为你添了白发簇簇 槐影凄凄也戚戚道破天机 我说我想逃到潮湿地 却独独不知 我心怀悲悯难捱的是你 夜呵万般静谧 未眠时刻奋笔仍惦念谁的不安稳呼吸 你究竟徒生多少惦记 圆了缺了碎了灭了暗夜里摇摇欲坠的跳动火星 还是梦国中阅后即焚的虚幻月影 我常画地为牢困在一纸文凭 血滚烫还是饮碎冰 你以环抱将我稳稳包裹住海风吻过檐角风铃 你说莫要误了花期盈盈 也常常恃爱而无忌争吵化作利刃潦草收场 却忘记疤痕尚痛痒 贫瘠破败的岁月有你挂念我便不会枕荒 柴米油盐染渍衣裳 骨皱腰痛琐事碎了肌理蚀眼角染了白发及肩长 在每个发起高烧的夜晚温巾敷额守在床旁 为我织就四季捕梦网 温脉一整个春天的minutiae 将破碎的我一一拼凑 送我到西洲 恩恩念念掬一捧香石竹天光得永昼 冰台色的绸 就在我推开门的那一刻 雨落了 /感恩/ 高一一班杜浩天 我钟爱天地之间的一切浪漫。四时更替,日出月落,晴空与浓云,微风和丝雨,都裹挟令我欢愉的情调。胡同小巷,破败砖墙,我每次路过要庄严沉思;梧桐松柏,榆柳杨槐,我看着它们学习如何生活。浪漫遁形在万物之中,可掌管它们的仙子总是给我开一道暗门,让我发现并享受无数美丽,于是我爱着世上万物。 可我唯独不喜欢花。橙黄红紫深深浅浅往眼里乱撞,像是醉鬼乱掷油漆桶的“杰作”,也有些素白或淡绿的花儿,可总是团团簇簇,早没了冰清玉洁的孤高之美,堆起来又成了好大好多的俗人眼里的盛景。于是每到花卉盛放的时节,听着人们不知是由衷还是附和的赞美,看着一拥而上的人群或近观或拍照,我总要叹一句:“不过是艳俗的蠢物罢了。” 转眼热风又拂过了初夏,赶着去明艳一池池芙蕖。牡丹花开了,聘聘婷婷地轻轻摇曳,娇俏动人。我陶醉地站在花前,看着国色天香的美人随风款款走近。我总觉这景象好不真切,想要再靠近些,却中了爱则难得的魔咒——一道道倩影娇笑着,摆出若即若离的姿态,不等我反应,便无声退后。 有趣啊,讽刺啊,我竟跌进了自己织就的俗套?事实上,我在初春时候便摒弃了自命孤傲的鄙夷,我开始对自己的浅薄感到后悔。 不记得具体的日子,只记得那些天总是没有太阳,枝头鲜少有新芽。室外的一切都无聊之至,又有着料峭的春寒,让我一刻也不想多待。 那天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走在了花畔。可能是因为刚搞了活动懒得走远些的路,也可能是因为听好多人说花开了而产生了好奇。总之我走在几株桃花和迎春花旁,极缓慢地蹭出每一步,目光终于还是定在了花枝上。 花枝棕里带粉,枝上零散地开着几朵花,都稚嫩得很,弹可破,吹即落。这个时节花苞更多些,它们较之花瓣似乎更结实些。花苞朝着天空,粉色的桃花苞和黄色的迎春花苞顶端都泛着红,在枝头如跳动的火苗一般闪烁。花苞确乎是火苗啊,它们点燃的是花火,燃烧着整株花树——星火燎枝头,燃得满树花。在这艳丽的火种旁侧,我嗅不到一丝烟火浊气,隐约有极清新的气息,似乎又含混着芳香——迥异于花店里叫人喷嚏连天的气味。 我的心和眼好像都被妖娆的迎春花枝条缠绕住了,朵朵桃花巧笑倩兮,娇羞又纯情,像是刚步入少女时代的小姑娘。我清楚自己此刻多半有了几分痴傻相,依然盯着花苞,瞟着花瓣。莫名其妙地,或是情难自禁地,我低声说了句:“让花火烧得再旺些吧。” 那个傍晚,一种未有过的欢悦上了心头,飘忽围绕许久。我不记得是怎么离开了几株花树,但我真真切切感到了不舍。我似乎不再对花感到厌烦,换言之,我成了一个爱花的人。 后面的日子,我并没有刻意到某株花前细观静赏,依然反感景点里招人蜂拥的花。但我常和路边街角的花儿邂逅,有的我早已熟悉,有的叫不上名字。我在连翘旁边驻足,为风雨打落的桃花默哀,拾起四月飘落的梧桐花,蹲身凝视纯白的小雏菊,又站到了牡丹花前。 我庆幸自己看到了花的绝美,花草之灵纯澈,濯人心而涤天地。庆幸的人总要感恩,我要感恩谁呢?是那天累人的活动,还是告诉我花开的师与友,抑或是自己喜好浪漫的性子?几度思索,上述种种均不能中的。 究其本源,是花苞的生机,鲜花的娇艳,晴朗时观者欣悦,风雨中凄美纤柔——自然天理之中的生灵与其姿态均平凡普通,人之所见都在常理之中,而最纯粹,最高妙的浪漫正在于此。是源于自然的纯净之美,让总自持清高的人放下了偏见,接受并享受着天地之间弥足珍贵的浪漫。 于是我要感恩的,是花,它们的美丽是浑然天成的,一切有关它们的浪漫心绪都是油然而生的。 一并要感恩的,是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 或许最应该感恩的,是这方藏纳乾坤,流转绚丽的奇绝天地。 /永恒的音乐啊,感谢你!……/ 高二二班姜芃湲 “音符跃动火树银花永恒的诗句” ——野蓝莓乐队《未命名的歌》 烈日,蝉鸣,吞噬着绿意的树荫。二楼窗口,一个穿着白T的背影靠在窗子上,抱着电吉他。小楼隔音不佳,时而有扫弦声传来。 这人正是徐帆,一百八十线摇滚小乐队的主唱兼制作人。乐队名叫野蓝莓(用鼓手小然的话说,这名字透着一股“莫名其妙的中二和神经质”),成立于五年前,徐帆的大学时代。乐队刚成立那会儿,夏日也同现在这般热烈。 “徐帆,咱啥时候开录,给个明白话儿呗!” 贝斯手程东的催促打断了徐帆的回忆。不错,现实又回来了:自己写不出好歌,乐队发出去的歌也没什么水花。他想着,叹了口气。 “开始吧。……小然和关关呢?” “关关她……没有跟你说吗?”程东直视着徐帆。 “什么?” 窗外蝉叫得更响了。 “她还是决定走啦。”小然走进来。 徐帆的眼神游走在他的鼓手和贝斯手脸上。说不上是难以置信,更多的是失落,自责。他能理解关关——乐队的吉他手,一个女孩子和三个大男人组个小破乐队,五年里一起默默无闻地搞音乐。此时的他更加痛恨起自己的无能为力,手里拎着的电吉他不小心“砰”地撞到墙上,在这长时间的静默里炸开一朵无声的落花。 “我知道了。今天我先录人声吧,顺便练一下关关吉他的部分。你们俩今天算是休一天假,明天录鼓和贝斯。”徐帆转过身去,望向窗外绿色的海洋。 小然和程东交换了下眼神。 门开了又关上,徐帆没回头。他以为是两人走了,回过身去拿歌词本,正对上程东厚厚的眼神。 “东哥……。” “你不要说什么了,我都知道。咱乐队也五年了,什么样的苦没吃过?我知道你难,我想你也知道大家都难。现在关关也离开了,这个样子下去,我们就算再怎么爱音乐,野蓝莓也走到头了。”程东顿了顿,咽了咽口水,继续说,“怎么说呢,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再试最后一次,下个月那张EP改成正专,如果再石沉大海的话,咱们乐队就散了吧。” 徐帆没回答。他和程东自打高中就是好哥们儿,大学时候他想组乐队,第一个就想到了程东。那些偷偷摸摸在管乐排练室里写歌、弹琴的日子,是他们心照不宣的回忆。 这一次沉默长达五分钟,但对于徐帆来说,他感觉像是一个世纪。扰人的蝉鸣在此刻仿佛也静默了下来。潮水一样向他奔袭来的,是不安、恐惧,还有渐渐深根发芽的决心。 “……好。”徐帆望着前方虚空,“东哥,那么就这一次,为音乐,拼一把吧。”他不敢去看程东真挚的眼神。 程东愣了愣,紧接着扬起了嘴角。徐帆不知道,可是他还记得。时空倒流五年,二十岁的徐帆也说出过一模一样的话。那时候还有更中二的下半句——“永恒的音乐啊,感谢你!……” …… 一年后,D市的一场音乐节上。 长长的节目单上,赫然用大字印着野蓝莓乐队的名字,旁边还用俏皮的字体备注着:年度新人乐队(获奖)。 徐帆、小然、程东坐在后台,休息区的电视正放着排在他们前面一个上台的乐队演出的直播画面。三人都抱着调好的乐器默默地看着。这时镜头切向观众,几个路过的工作人员看见后低声惊叹:“天啦,野蓝莓还没上去那边舞台就那么多人等着看!” 徐帆不知该说什么。去年的那张呕心沥血、孤注一掷的专辑——《未命名的歌》发行之后,第一个月仍然是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ingchunhuaa.com/ychpz/8251.html
- 上一篇文章: 你没看错,这次二外是真的要选校花了
- 下一篇文章: 最适合儿童语言启蒙的材料,还是它